文章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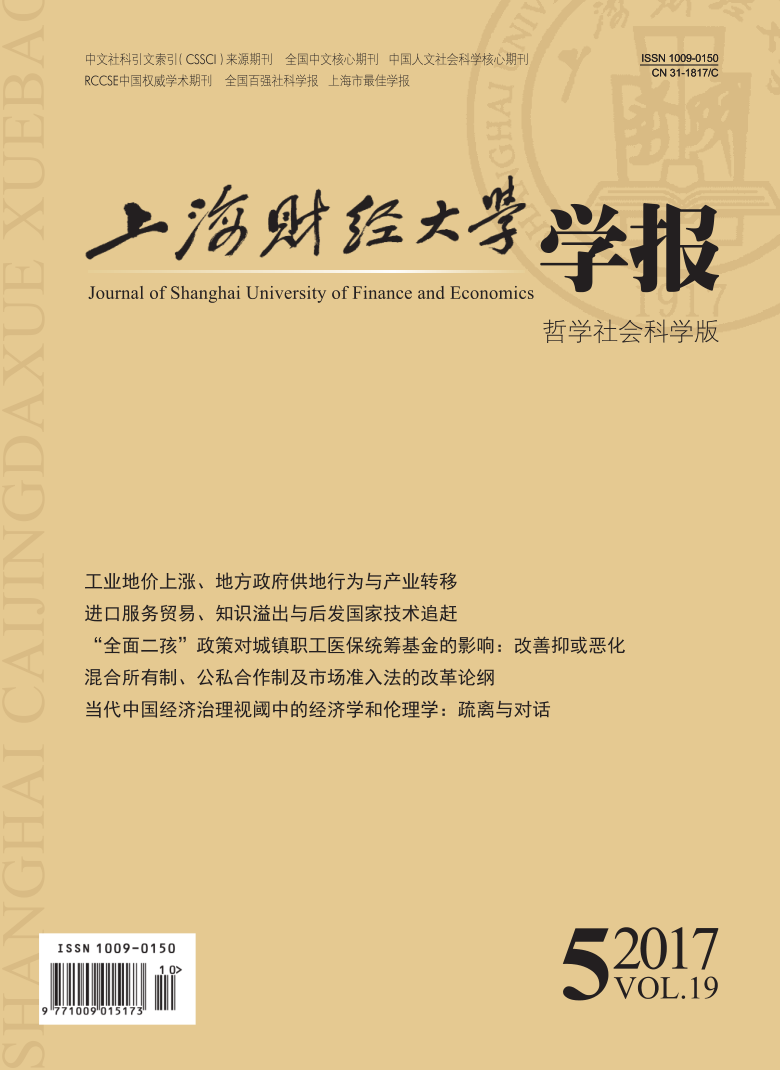 | 上海财经大学 2017年19卷第5期 |
- 陈琳
- Chen Lin
- 当代中国经济治理视阈中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疏离与对话
- Economics and Eth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Economic Governance: Alienation and Dialogue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7, 19(5): 116-128.
-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7, 19(5): 116-128.
-
文章历史
- 收稿日期:2017-05-13

2017第19卷第5期
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中国高校演讲时,把曾经询问美国大学生的一个市场伦理问题抛给了中国大学生:如果发生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商家可否大幅度提高雪橇的价格?让这位教授感慨的是,中国大学生回答“可以”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大学生,而其主要依据则是“加价可以平衡供求”这一经济学原理。不难理解的是,中国大学生对这一原理的信赖以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中国经济成就为其宏观背景。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有着更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美国,其大学生反而对市场更加“不信任”?对于类似问题,经济效率是否是最重要的决策标准,市场在其中应有怎样的角色?
这些问题对当代中国经济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市场体系的快速引入,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制度支持,也为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带来了如何平衡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的现实难题。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收入差距扩大和阶层固化的背景下,经济与伦理的高墙隔离正推动着每个当代中国人在物质膨胀中精神缺失的割裂感,并汇集为浮躁、复杂的社会心态;对中国经济治理的政策和学术讨论,也从关注总量增长转向调整产业、区域、分配和动力等结构性问题,并涉及经济学不同流派围绕市场制度的争论。对经济学和伦理学关系的反思,有助于为个体理性平和看待市场经济提供思路,也可以为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启发。
我国国内对经济伦理问题的专门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现有文献可以被概括为三大类:第一,从应用伦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侧重探讨不同经济领域或经济主体的具体商业伦理问题;第二,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指新古典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关注市场与政府、公平与效率、文化与制度等宏观层面的经济伦理问题;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进行的研究,指出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掩盖了对社会基本制度的批判,从而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真正的社会公正。
从文献数量和学术影响力上看,第一类研究具有绝对优势,其他视角的成果相对缺乏,不同视角之间的对话更加缺乏;倡导价值中立的经验研究方法论在当前国内经济学教育、学术与实践领域依然拥有强势话语权,较为缺乏能够与主流经济学对话的经济伦理研究。从具体观点来看,国内学界不同视角的经济伦理研究在价值理念和现实可行性上仍有较大分歧,在学科分工和教条偏见的推动下,这些分歧还有发展为看似不可调和矛盾的倾向。加强跨学科研究已是国内经济伦理学界的共识。
从国际视角看,虽然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困于伦理与市场之间张力的困扰,但从亚当•斯密到约翰•梅纳徳•凯恩斯,不少经济学经典大家都对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有诸多涉猎。边际革命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逐渐摆脱宗教伦理、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价值批判的束缚,成长为道德无涉的经济科学的帝国。在这一背景下,伦理学和经济学在现代西方学界也长期彼此隔离——前者批判后者缺乏道德关怀,后者则认为前者不是从理性角度探讨有实践意义的科学问题。“去伦理化”使新古典经济学演变为“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①,并有力推动其影响力的迅速扩张。
①Robinson, J., Economic Philosophy, London: C. A. Watts, 1962: 7-10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经济政策失灵和社会利益分化所带来的实践难题,国际社会开始从伦理视角重新审视市场经济体系,对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探讨随之繁荣。当前,该领域的研究依然百家争鸣,大体上可归结为三大类:第一,从思想史角度阐释经济议题和伦理议题由合而分的过程和原因,借此展示西方主流经济学去价值化的历史性和局限性;第二,对个体经济理性的伦理内涵进行价值清理,并结合心理学、行为学等领域的实验研究对其进行经验检验;第三,从企业伦理和市场制度角度的应用性研究、从哲学认识论角度进行的方法论探讨等。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从经济思想史、具体理论和当代中国实践三个角度阐释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和国内现有的经济伦理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提供了一个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伦理研究框架,从而为我国国内哲学和经济学关于经济伦理问题的良性对话提供了可能。具体包括:第一,从思想史角度揭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以及走向疏离的历史原因;第二,从目标最大化、不完全契约和激励相容这三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视角,阐释伦理学与经济学对话的理论依据;第三,结合当代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相关公共讨论,阐释经济学与伦理学对话的现实意义。
二、从思想史角度看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离经济学脱胎于人类对善治的追索。何为善治?古老智者着眼人性,现代智慧关注制度。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治的标志在于“教人习善”②,孔子则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然而,两千多年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指出善治应是一套无需让人们“变得更好”的制度体系③,如何构建这一制度体系已俨然成为当代社会争论的焦点。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疏离内嵌于善治之道的这一转变过程之中,与其互为因果、互相推动。
②Aristotle, translated by W. D. Ross, Nicomachean Ethics,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1999: 21.
③Hayek, F A.,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11–12.
(一)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离:过程与表现被现代经济学奉为鼻祖的亚当•斯密是《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巨著的作者。经济问题和伦理问题似乎都困扰着这位生活于18世纪的古典哲人,也激发着其灵感,但半个世纪后,它们逐渐走向疏离。19世纪中叶,约翰•穆勒在面对经济学和伦理学是分还是合这一难题时还犹豫不决,他不仅为其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后缀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这一副标题,还在论述中多次表现出两难情绪:既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同社会哲学的很多其他分支不可分离地纠缠在一起的”、“全部间接地有联系并且相互影响”,又指出它们是“有本质上区别的”、“完全不同的”问题①。到了1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则不仅简洁地把其著作命名为《经济学原理》,还干脆利落地指出,“经济学的规律是以直述语气表达的倾向之叙述,而不是以命令语气表达的道德上的告戒”②。虽然在这一时期也还有亨利•西奇威克这样在经济学和伦理学两个领域同时颇有建树的学者,但是经济学和伦理学已经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注定走向殊途。
①Mill J 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John W. Parker: 7–13.
②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890: 7–10.
这个新时代以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义为开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表达经济规律之“语气”不同于伦理学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本性的不断变化和细微的力量”,所以“当然不能和精密的自然科学相比”;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利奥尼尔•罗宾斯已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论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其中,他在批判了一系列含糊不清的界定后,明确指出“经济学是从稀缺资源配置角度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并指出“经济科学在本质上不同于伦理学”③。这一思路被约翰•希克斯等数学家发扬光大,到了20世纪中期,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联系几乎消解殆尽。
③Robbins, L.,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2:15, 31, 132.
此后至今,虽然不断有“异教徒”想要回到亚当•斯密那被经济和伦理盘根错节所缠绕着的大脑中探个究竟,但他们的尝试都未曾妨碍主流经济学沿着价值无涉的方向大步前进。2009年,萨缪尔森在其流行教科书的前言之前还新添了一篇“一个折衷主义者的宣言”,明确宣称:“本书倡导的折衷主义并非是由意识形态所培育的,我们只根据现实和理论来推定自由或官僚主义的客观后果,所有读者都可据以自由地择定他们心中最好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我们的作用并不是要改变他们的价值观”④。
④Samuelson, P A., Nordhaus, W D.,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9: 23.
(二) 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疏离:背景与原因对于亚当•斯密而言至少与经济问题同样“令人烦恼”的伦理问题,为什么在经济学的后续发展中被一步步驱逐,直到毫无容身之地?这个问题引导我们再次回到有关善治的话题。对古典哲人而言,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张力在于二者蕴含着对“何为善治”的不同解答,前者要求“导之以利”,后者则要“教之以德”。如何选择?亚当•斯密极为矛盾,他撰写了分别关注伦理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两本著作,同时使用自利和同情来描述人性。事实上,对伦理的疏离在亚当•斯密这里已现端倪:他在写作《道德情操论》的20年后写了《国富论》,对于前者而言是核心概念的“同情”、“仁慈”等观点在后者中被淡化和不再产生直接影响。
置古典经济学于其思想史背景之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微妙的转变酝酿于现实主义风气在欧洲思想领域中的兴起。16世纪初,面对诉诸伦理的治理方式所遭遇的现实挫折,尼科洛•马基雅弗利否认了亚里士多德以公民品格作为善治基础和目标的观念,称善治应该秉持为恶人立法的原则。大约200年后,伯纳德•曼德维尔把这一原则改造为更广泛传播的激进版本,宣称恶德是繁荣之源,大卫•休谟则把其概括为“为小人立法”①。紧接着,杰瑞米•边沁提出要让人们的义务与利益相一致,亚当•斯密则用更广为人知的“看不见的手”描述了如何铺就实现该目标的道路,现代经济学由此发芽。对“看不见的手”的证明、补充和拓展至今依然是经济学的主流。难怪列奥•施特劳斯说“经济主义是发展成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②。
①Hume, D.,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39.
②Strauss L.,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39
置古典经济学于其思想史背景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催生于古典经济学家们在探寻善治之道时谨慎而又心切的道德敏感。尼科洛•马基雅弗利所倡导的现实主义转向源于对“教人习善”这一目标的可行性的忧虑。基于倡导公民品格并不足以保证善治的历史考察,16世纪以来的思想者们一跃而认为只有良法才能确保良治。巴鲁赫•斯宾诺莎在17世纪就指明了该飞跃背后“不能按照理想人性来进行治理”的务实精神③,进而架起了从16世纪尼科洛•马基雅弗利到18世纪亚当•斯密的桥梁。
③Spinoza, B.,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Ethics and Correspondence, Translated by Elwes, R. H. 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55: 32.
当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候,他关心的已经不是人性能否达到《道德情操论》中的理想状态,而是如何限制其在最差状态之下的作恶机会。谨慎的态度促使他寻找无需依赖于德性而实现善治的可能。于是,关注点从培育德性转向了利用恶习。而在人类的诸多激情之中,基于贪婪的自利似乎已是最无害和最可被引导的一个了——贪婪在中世纪被看作是七宗罪中最轻的一个④,托马斯•霍布斯也早在亚当•斯密之前就指明了贪婪对和平的可能贡献⑤。在该思路的引领下,经济学终于把善治发展为价格和产权、税收和补贴、奖赏和惩罚等一系列通过引导个体自利来实现社会公意的制度总和。善治与公民品格不再相关。在亚当•斯密之后短短两个半世纪的今日,自利与贪婪划清了界限,甚至原本催生了经济学本身的道德敏感也逐渐淡化和消退。
④Bloomfield, M. W., The Seven Deadly Si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a Religious Concep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Press, 1952: 65.
⑤Hobbes, T., Leviathan, London: Continuum, 2005:107.
三、从具体理论看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面对善治的难题,主流经济理论把其分解为两个部分:何为善、如何致善。效用论被用以应对第一个问题,即效用就是价值;理性选择被用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即个体基于第一步给定的效用、在可替代方案中找出能够致善的最有效途径。在这里,目标外生和自由选择共同竖起了善治与伦理之间的高墙,理性自利则被作为撬动公共利益的支点,整个架构不乏四两拨千斤之美感。自亚当•斯密以来,这一框架在赞扬和批评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治理方式的演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遗憾的是,该体系至今仍未能完成“借自利之力以达善政”的重任,而阿喀琉斯之踵恰恰就在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裂痕。
(一) 目标为何难以外生:无处不在的价值内涵熟知现代经济理论的人并不会因“经济学认为人都是自私而只懂得算计的”这一批评而大发雷霆。毕竟,不知者不为过。确实,和感慨“大多数人都是很坏的,是逐利的奴隶,是险境中的懦夫”的亚里士多德相比①,为现代经济理论打下地基的古典哲人们显然对人性更为乐观:尼科洛•马基雅弗利说“人们很少能够完全为善或者完全为恶”②,大卫•休谟认为常见于政治学的“小人假设”在现实中并不真实③,亚当•斯密则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就指出人类具有关心他人福利的本性④。
①Aristotle, On Rhetoric,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Appendices by Kennedy, G. 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129.
②Machiavelli N., Discourses on Livy, Translated by Mansfield, H. C. and Tarcov, N.,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73.
③Hume D.,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7: 39.
④Smith, A.,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Penguin, 2010: 1.
更为重要的是,在后续两个多世纪的风吹雨打中,前仆后继的追随者们早已对理性自利进行了高强度的加固和清理,使其与自私之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在现代经济理论看来,经济理性不同于一般情形下人们所理解的心理理性,也即并不强调思考(抑或算计)的心理过程,而只是用目标、偏好和约束来描述人类行为。经济理性所描述行为的伦理维度非常丰富:既可以是批评者眼中的损人利己、寄情物欲,也可以纳入习惯和规则,可以因偏好利他而奉献,可以因偏好闲暇而不贪婪,甚至可以只是其分析方法所描述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不同情境中的具体含义则由行为者自行决定,被打包于个体效用之中,外生于对选择行为的分析。
基于此,经济理论得以把难解的伦理问题在分析开始之前就丢给了行动个体,后续研究的价值无涉也就不证自明。然而,妨碍着经济与伦理彻底分离的正是这个被用以囊括所有伦理维度的关键概念:效用。对效用的常见描述方式是针对其具体内容的,例如快乐、幸福等某种主观现象,或依照习俗、权利、义务、绝对命令等原则而达成的某种客观行为或者状态。与此不同的是,经济理论采用抽象方式描述效用,即把其界定为某个分析框架下的偏好排序。但这个方法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都面临挑战。
先看内部的技术挑战。首先,用一般简单技术界定的某个偏好排序只能对应复杂多样的具体效用中的某一种,高阶偏好等更为复杂的数学方法虽然可以纳入更多维度,却仍无法解释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如果采用多层一致偏好,那么在逻辑上就与单层偏好没有本质差别;如果对不同维度赋予不同权重,则无法回答权重从何而来。其次,从个人效用上升到社会层面,还需要应对效用是否同质、如何进行个体间比较和构造社会福利函数的难题。最后,整个抽象框架的运转依赖于完整性、可传递性等对人类心理的假设,但是它们的真实性受到心理学实验的挑战。
再看外部的价值挑战。用基于偏好的抽象排序来描述幸福感基本没有问题,但是权利、习俗、规则等也可以被纳入抽象偏好排序吗?即使能够克服所有技术难题,依然无法避免一步步的伦理追问:能够被更高阶偏好所支持的效用就是有价值的吗?把所有价值主观化的过程是否已经吞噬了这些伦理本身的内在意义?面对这一系列诘问,确实有经济学者坚持所有伦理都可以被理性自利来解释。他们或者认为道德本身就是理性自利在社会进化中进行选择的结果,或者认为那些明显与自我利益相违背的牺牲已通过带来心理满足而与理性自利达成了一致。对于前者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已经彰显了其价值判断,而后者难免陷入“所有人类行为都有其相应心理过程”的逻辑。
总之,给定现有的效用理论,试图无涉价值的具体经济分析却无不弥漫着从内到外的特定伦理气质。事实上,古典哲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一难题,并基于此给经济学定下了谨慎而谦虚的基调:约翰•穆勒说,“政治经济学并不研究人类本性的全部,而只是关注由想要占有财富的欲望所驱动的部分,它只预测那些由于追逐财富而导致的结果”①。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表示,“经济规律和推论事实上不过是良心和常识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和树立可以指导生活的那些法则的资料之一部分而已”②。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经济学如今已经戴上帝国主义的皇冠。基于特定抽象框架及其所对应特定伦理内涵的所有研究都被咄咄逼人地冠以社会福利或公共利益之名,混淆于其中的伦理维度让讨论变成了聋子的对话。
①Mill J 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John W. Parker, 1852: 7–13.
②Marshall, 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890: 7–10.
(二) 为小人立法何以难达善治:不完全契约下的不可能三角现代主流经济理论的真正信仰者大概也不会认真对待上述对效用论的质疑。在《福利经济学》中,阿瑟•庇古还试图厘清效用、满足、欲望等这些他从前辈那里继承而来的词汇的含义,但很快就得出“用词问题是次要的”这一结论,并大踏步走上了寻找“没有任何伦理暗示”的用语的征途③。自此以后,除了阿马蒂亚•森等少数同时涉足哲学和政治学的经济学者之外,现代经济学似乎已经放弃了对效用概念的真诚反思——哈耶克明确嘲讽劳动价值论不是在讨论真正的问题,而是在探讨“虚无缥缈的价值问题”④。
③Pigou, A.,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2: 23–30.
④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40–47.
这么做也许并不是全无道理,因为经济理论的精彩之处并不在于对效用和价值的分析。试想,如果有一种制度安排可以在当所有人都只在意自己利益的时候依然达成公共利益,那么,上述关于理性自利和主观效用的争论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如果个人偏好的具体内容与社会公意无关,那么,把它的决策权留给每个具体的人不是最好的选择吗?现代经济理论的最美妙之处,就是试图搭建一套对个人偏好不设限而达成帕累托效率的社会系统——市场。罗拉尔•德布鲁在20世纪50年代宣称自由主义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数学证明,其依据就在于,福利经济学第一和第二定理表明,个人最优(效用最大化)与社会最优(帕累托效率)一致,而且可通过调整初始禀赋实现任何公正目标。
然而,该定理的证明以“存在完全竞争、完全信息、没有外部性的完美市场”为前提。用更为简单的语言概括这一条件,也即:凡事皆有价,价格没有错。确实,如果社会公意要求个人所做的一切都可被给出合理的价格,也即实现所有外部性的内部化,那么市场也许真的可以替代伦理。问题在于:如何达成这两个条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认为只要一个守夜人政府就已经足够,而在差不多正好200年后,肯尼斯•阿罗和弗兰克•汉恩则指出:众多对“看不见的手”的推崇和证明,可能只是说明了其运转需要什么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在现实中又是多么难以实现⑤。
⑤Arrow, K. J. and Hahn, F. H., 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 San Francisco: Holden Day Publisher, 1971: 5.
这些发现带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现代经济理论转而关注如何设计由产权、税收、补贴等构成的“激励相容”机制,以辅助市场制定正确的价格。遗憾的是,信息和激励理论发现这只想要助市场一臂之力的有形之手也颇为乏力,因为其有效运转同样需要前提条件:第一,能制定出完善的激励机制;第二,能实现对激励机制设计者本身的有效激励和监督。由于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可向第三方验证等不完全契约的约束,这两个条件在现实中常常难以被满足。于是,界定产权和设定奖罚的成文制度与政策不再是给出合理价格的保护伞,公司治理和金融监管成为影响当代经济运行和可能引发经济风险的关键。早在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说明就直陈,“莱昂尼德•赫维奇的一篇文章证明没有任何满足参与约束的激励相容机制能够实现帕累托效率”,让•雅克•拉丰等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模型当中,帕累托效率和自愿参与是不相容的,即使是在没有公共品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近期,鲍尔斯•塞缪尔则直接把不能同时达到“自愿参与、偏好不受限和帕累托效率”这三个目标的困境概括为“不可能三角”①。
①Bowles, S., The Moral Economy: Why Good Incentives are no Substitute for Good Citize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28.
(三) 向贪婪借力的代价:激励相容的负作用就这样,不完全合约的困境犹如当头棒喝,惊醒了“为小人立法而达善治”的南柯一梦。对于惊醒的梦中人而言,迈克尔•桑德尔对“金钱不能买到什么”的提问、德伯拉•萨兹对于“为什么有些东西不能出售”的论证可能有一定的启发。确实,激励相容机制希望以物质奖惩为杠杆、以理性自利为支点撬动人类行为,进而实现公共利益,这里的潜在假设是物质激励和影响人类行为的非物质因素互不干扰。但是,人类复杂的行为动机并不满足分布的可加性。20世纪70年代起,外在激励会挤出内在激励逐渐成为心理学的常识,虽然经济学家理查德•迪马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也借由引入献血价格反而降低了献血总量的分析,提醒人们注意依赖价格的公共政策的负作用②,但直到20世纪末,这一问题才真正进入主流经济学界的视野,并逐渐引起较大范围的重视③。
②Titmuss, R. M., The Gift Relationship, New York: New Press, 1970.
③Kreps D. M.,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Extrinsic Incentiv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87(2): 359-364.
目前,内在激励已经成为经济激励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薪酬合约设计、人员效率匹配和公共品供给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把其纳入经济学经典理论框架的愿望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事实上,这些尝试本身就推动了前文关于不完全合约之下难以制定正确价格的发现——内在激励本身就是导致严重信息不对称和不可验证性问题的核心来源。到这里,经济学也许到了不得不放下帝国主义的束缚而与人类智慧的其他分支共舞的时候了。
鲍尔斯•塞缪尔的尝试颇有启发。他和合作者们特别关注了责任、公平、利他等伦理维度的非物质行为动机,用“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一词对其进行描述,探讨了物质激励对这些因素的影响。对大量经济学实验结果的再分析表明,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物质激励对社会偏好的负面挤出作用,究其原因,正是哈耶克所津津乐道的价格的“信息”作用。首先,激励机制揭示了其设计者的信息,例如设计者自身的特征、对被激励者的预设、想要让被激励者达成的任务的本质等,而被激励者常常把物质激励的出现和提高解读为关于任务正当性和委托—代理双方信任感的“坏消息”,进而损耗社会偏好;其次,市场价格和交易让行为者与最终后果之间产生屏障,进而提供实现道德无涉(moral disengagement)的机会,或者说行动者往往把奖励或者惩罚当作贿赂、奖赏和工资,从而取代社会偏好;再次,激励意味着控制,会威胁被激励者的自治感,并让被激励者对自己“出于善意而行动”的动机产生自我怀疑,降低社会偏好的自我认同和行为动力④。
④Bowles, S., The Moral Economy: Why Good Incentives are No Substitute for Good Citize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1-166.
简言之,依赖于经济激励的公共政策往往对公民品德产生负作用,而当这些负作用累积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从“为小人立法进而让坏人像好人一样行动”的出发点,意外走到了“生产小人并让好人像坏人一样行动”的世界。卡尔•马克思说物质生产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已看到了关键所在,罗伯特•卢卡斯在提醒人们注意政策对预期的影响的时候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但现代经济理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可能更为残酷:霍布斯所假设的野蛮人可能更是霍布斯主义治理方式的结果而非原因;或者说,不是纯粹经济理性人(homo ecomicus)在一个遥远的过去发明了市场制度,而是由理想经济模型所搭建的公共政策架构导致道德退化和狭隘自利不断蔓延。难怪爱德蒙•伯克感慨,随着市场的兴起,骑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而更让人唏嘘的是,不光是其所构建的社会体系,由寻求善治之道所催生的经济理论本身也不知不觉在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早有研究发现,仅仅是更多接触现代经济理论本身,就可以让人更认同理性经济人而缺乏伦理关怀①。
①Frank, R. H., Gilovich, T., Regan D. T., Does Studying Economics Inhibit Cooper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3, 7(2): 159-171.
也许,是时候重拾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初的道德敏感和谨慎态度了。即使是尼科洛•马基雅弗利这位“为小人立法”的始作俑者,也在言语中透露出对于单凭法律而达到“刁民下的良治”的不信任,不时表现出良法(good law)与良俗(good customs)是互补品而非替代品的忧虑。大卫•休谟更进一步指出连市场本身的良性运转也离不开伦理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说,“法律作为阐明的规则,不会完全替代未阐明的规则,而只能在一个尚未阐明的规则的框架内发挥作用并得到理解”②。这提醒我们,要做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共政策,就离不开对经济问题和伦理问题的统筹考虑。
②Hayek, F. A.,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2): 129.
四、经济学、伦理学的对话与当代中国经济治理 (一) 直面“不可能三角”和挤出效应:让经济嵌入社会上文已说明,在普遍的不完全契约情况下,自愿参与、偏好不受限和帕累托效率难以共存。主流经济理论应对这一困境的方法是放弃帕累托效率。200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说明指出,“在参与者有私人信息的时候,经典意义上的帕累托效率无法达成,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效率的新的标准”,后续的激励理论转向了激励效率(incentive efficiency),即给定行为主体对激励的反应时所能达到的最佳结果。确实,催生现代经济学的道德敏感时刻提醒着经济学者,对参与或者偏好进行干预(甚至发表意见)是极为危险的。所以哈耶克说,社会公正“似乎已经是普通大众所能理解的唯一辩护词”,这也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学说“扎根最深、影响最坏”的话语,因为“只要社会公正的信仰主宰着政治行为,社会就存在着走向集权主义的倾向”③。
③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40-47.
然而,虽然主流经济理论认为“次优状态”也不失为一个出路,却难逃他人把此看作“一场由于病人消失而成功的手术”的嘲讽。依然选择坚守帕累托效率和自愿参与的市场体系的经济学者则表示,人们会在社会和个人的漫长互动过程中领悟理性自利的真正内涵,进而习得与社会利益相一致的个人偏好。当然,这一从社会利益倒推出的个人偏好,自然不会再受制于“不可能三角”。类似的,当法学家和律师们指出,是“作为原则的法治”,而非“作为既定规则的法制”才是善治之道时,正如蒂姆•贝斯利所言,经济学已经为伦理学递上了邀请函④。这一结局被鲍尔斯•塞缪尔戏称为“经济学唤回亚里士多德”。
④Besley, T., What’s the Good of the Market? An Essay on Michael Sandel’s What Money Can’t Bu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3, 51(2): 478-495.
与此同时,即使是在完全契约下,激励相容机制也可能产生挤出内在激励和社会偏好的负作用。价格的信息功能提醒我们,问题可能不出于激励本身,而出于设计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激励所传达的信息。所以,要降低和避免挤出效应,甚至让物质激励和社会偏好相互促进,就需要想方设法抵消物质激励中可能蕴含的负面信息。例如:表达对被激励者的信任和阐释任务本身的正当性、给予被激励者参与激励机制设计和与既定规则对抗的自治机会,强调惩罚和奖励都无法替代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及其社会评价,甚至彰显激励者为执行激励所承受的代价①。这些“技巧”的共同点,是让物质奖惩成为伦理的载体而不是替代品。其实,当我们理解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时候,就体会到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共舞的美妙之处。
①Bowles, S., The Moral Economy: Why Good Incentives are No Substitute for Good Citizen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170–180.
明确引入伦理维度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可能是件新鲜事,但是对公共政策整体并不新鲜。人类历史上鲜有小人之国的长久物质文明,教育、宗教等社会体系也都以影响人的道德素养为本。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避免走入完全否定经济激励的另一个极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倡导“教民习善以达善治”的雅典城邦,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陌生人交往的增多,历史已经证明了单纯依靠德性治理方式的失败。近代以来,以改造人性为公共政策之直接具体内容的大规模尝试无不惨遭失败,因此,其有着深刻的教训。物质动机至少在现阶段肯定还对人类行为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解释力,这意味着经济激励在当代公共政策中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我们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对话中获得的最重要启发,应该是卡尔•波兰尼(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不受任何限制的市场乌托邦大唱赞歌的同一时期)所说的“嵌入社会的市场”。市场只是嵌入公共治理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它需要和其他部分协调运作才能带来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转。让市场替代政治、道德、宗教、社团等其他治理方式的尝试,其结果可能与政策制定者本身的愿望南辕北辙。这可能部分解释了把非洲原始部落中原本依靠国家和社群进行治理的公有产权强行改变为私有产权所导致的问题。弗朗西斯•福山指出,“最早的私人财产,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宗族或其他亲戚团体,主要动机不是经济的,而是宗教和社会的,渴望得到地产,不仅是为了其生产力,而是为了死去的祖先和不可移动的家灶”,“在北非,新移民不是通过买卖,而是通过加入当地社团的礼仪以取得土地使用权。在运转良好的部落里并不存在公地悲剧。西方人未能理解共有财产的性质,而一味强制在非洲建立所谓的现代产权,或多或少是非洲目前政治失调的根源之一。”②
②Fukuyama, F.,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54–60.
(二) 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对话:以所有制问题为例我们从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纯理论探讨回到了现实,且碰到了一个可能对当代中国经济治理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所有权制度。当前,我国国内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依然剑拔弩张。一方面,私有产权被视为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根本性前提,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有碍公正的情况一再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另一方面,公有制度则被视为克服市场经济弊端、彰显社会主义伦理优势的唯一方法而不容争论。当这场只有立场对峙、没有良性讨论的“聋子的对话”在理论界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实践领域那些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过程中的、不得不行动的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如果还没有在机会主义策略引诱之下走上为积攒个人利益而浑水摸鱼的钢丝绳,就只能在寻求善治的道路上腹背受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知如何是好。这些依然是苦寻善治之道的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可能正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不断扩大的裂痕;而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对话,也许能让这些为难的人们感受到一些温暖的力量,也为开启良性对话提供可能。
从思想史角度看,对于所有制度的理论争论起源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相较于效率目标,从亚里士多德到约翰•洛克的无数智者都更青睐于私有产权的伦理正当性。他们指出:个人物品对于个人发展必不可少,而在资源稀缺、个体间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差异化的分配;个体劳动创造了产品,进而使得占有具有了正当性,而个体间劳动能力的多样性则决定了所占有产品的不平均;个人占有物品是自由的基础、自爱的延伸。但从卢梭到蒲鲁东等也对上述理由一一进行了驳斥:基于个人发展所需的有限“占有”的正当性无可置疑,但是不受限的“所有”只会导致物欲膨胀和道德退化;个体劳动能力的形成源于对资源的消耗,资源有限意味着产品有限、能培育出的劳动能力也有限,这意味着个人劳动能力不均是资源占有不均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私有产权才是导致奴役和不自由的根源,也是导致平衡的自爱发展为极端的私欲的推动力。可以看出,私有产权的支持者强调“占有”的必要性和个体间禀赋的多样性;公有产权的支持者强调“所有”的现实性以及个体间权利的平等。分歧源于现实的无奈:给定目前的技术和制度情况,“占有”往往借助于“所有”来实现,同时,资源限制导致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仍无法实现,分配问题在所难免。这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捍卫私有产权的思想史背景。
从实践角度看,包括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内的前计划经济国家所遭遇的滑铁卢给人类智慧的最大启发,大概就是私有产权在当代社会提供有效激励的效率优势,新制度经济学把这一收获概括为“私有产权带来经济效率”的著名“科斯定理”,在公共讨论中得到快速传播并广受推崇。有趣的是,罗纳德•科斯在其诺奖获奖感言中强调,他自己并不赞成“由乔治•斯蒂格勒命名和形式化的声名狼藉的科斯定理”。其核心原因就在于,这一定理具有苛刻的、现实往往无法满足的前提条件——交易成本为零。前文所论及的不完全契约正是导致高额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所以哈耶克也说,“传统的财产观是一个内容多变而极为复杂的包裹,至今仍未发现它在所有领域最有效的组合方式。如想让分立的财产制度实际发挥出它的最佳效果,文化和道德的进化确实需要更上一层楼”①。
①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23–27.
确实,私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有效运转都离不开一定的道德关怀。本文第二部分已经详细阐释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体系为何无法与伦理划清界限。对于公有产权而言,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其早期支持者的论述,就会发现,其对公有产权的支持同样依赖于伦理假设,甚至可以说,他们对公有制之下激励失效这一挑战的回答是釜底抽薪式的: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劳动原本是人类本性的需要,需要物质奖罚的劳动恰恰是依赖于经济激励的整体制度框架(私有产权是其基础)挤出了内在激励的结果,是人及其劳动被异化的表现。也正是基于此,才有《共产党宣言》在提出“消灭私有制”时的冗长前缀,以及给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出路②,才有前南斯拉夫总理对于教条主义理解公有制危害的警告和对马克思提出公有制的原本用意的提醒③。
②《共产党宣言》两次提及所有制,第一处:“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第二处:“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个人拥有财产非但不是什么耻辱的事,反而是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③卡德尔在《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中说:“把公有制说成是某种静止的形式或教条,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社会实践中,这样的出发点甚至可能变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停止因素。公有制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总和。公有制的历史含义在于克服劳动同社会资本的异化”。
到这里,我们终于体会到了保罗•卡恩所说的“话语的二律背反”①。此时,如果能够放下争论中的情绪、秉承休戚与共的态度着眼于共同的未来,就会发现双方并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冲突,而只是在争论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看似剑拔弩张之下,是一样的寻求善治之道的热忱。走出教条主义的迷雾,双方也就会理解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在确保技术持续进步的其他建制(如科学方法、大学、人力资源、鼓励探险和试验的文化氛围等)尚未问世时,单凭良好产权所创造的生产效率提高仍然有限”②,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说的,对于所有制而言,“政府、私人和社区控制在某些条件下都能起到作用,它取决于我们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的自然状况”③。也就是说,私有产权必须嵌入相应的公共治理系统才会有效,而且所有权的具体安排要因地制宜。这时,双方就可以把精力放在整体制度架构的系统建设,以及对所有制在一个个行业、公司、社区层面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上(也即研究如何“重建个人所有制”),意识到所有制问题的最优安排尚需人类智慧,进而更全力以赴地关注于私有制和公有制同样面临的组织和激励难题。这时,没有了“经济至上”和“伦理之上”的门派之争的保护,那些为着一己私利而浑水摸鱼的投机者也就无所遁形了。
①Kahn, P. W., Putting Liberalism in Its Pl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5–129.
②Fukuyama, F.,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167.
③Ostrom, E.,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1-10.
五、结 语回看历史,现代经济学萌发于对经济问题与伦理问题之间张力的沉思,由追求自由、平等的道德敏感所催发。但在特殊的历史背景、思想者的谨慎态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变迁的推动下,终于演变为近现代人类在价值无涉基础之上构建良善生活的尝试。无数智者和勇者为此献身,他们的研究连同市场及其当中的经济理性一起,也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做出了不可置疑的贡献。但是,经济学、伦理学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及相应的公共讨论和公共政策也带来了诸多问题:经济问题的去价值化推动区域间冲突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不断升级;伦理问题的去现实关怀则导致宗教冲突在信仰即真理的信念下陷入无法沟通的绝境;而无数投机主义者,正在这个充斥着立场对峙、缺乏良性对话的迷雾中趁火打劫、中饱私囊。
在亚当•斯密之后两个半世纪的今日,当主流经济学集诸多英才之智慧试图寻找一个保障绝对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三者共存之铁律的努力在遗憾中宣告失败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得不再次回到经济学诞生的起点,直面那份催生了经济学科的伦理关怀。这次,我们依然要审慎地警惕伦理讨论中非常容易产生的道德压迫和随后的强制行为,同时,也具有了经济理论在这两个世纪的发展中给予我们的启发:伦理讨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的简单争论、压迫说服和利益妥协,也在于运用科学精神对“为什么这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认为”、“现实操作该如何进行”等问题的事实描述、因果探讨和逻辑清理,也更在于在尚未找到合适行动方案和政策设计时保持宽容、谦虚和审慎。这次,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在面对个体生命和公共生活本身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的时候,单纯的理性或热情都不足以帮助我们走向良善生活;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散发着理性光芒的冰冷解剖刀,也有决定着这刀划向何处的温暖的爱的力量。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对话在西方已经逐渐兴起并开始引起关注。而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真正接触“现代市场体系”的中国,还依然在经济学和伦理学继续撕裂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快速的市场化过程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忽视经济问题所导致的惨痛教训一起,把经济理性深深植入每个当代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也把伦理关怀悄悄藏了起来。这就难怪,面对迈克尔•桑德尔的雪橇难题,中国年轻人对于“涨价不为过”这一市场选择的支持率远高于美国年轻人。当经济学与伦理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汇集起来的时候,我们也不难理解教育、医疗、养老和所有制等改革深水区所面临的困境。放下不同学科的傲慢和偏见,跨过学科隔离的高墙,对当代中国经济治理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当科斯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关于“中国缺乏自由思想市场”这一批判被广为引用的时候,我们也应注意到他用以结束这一探讨的话语:“具有批判思想,愿意挑战权威,而又宽容、虚怀若谷的公众,才是自由思想市场发展的沃土”。这提醒我们:自由市场和公民品格互为支撑,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对经济、伦理及其互动的统筹考虑。这并不容易。但是除了尝试,我们别无选择。好在,我们并不完全是白手起家。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酝酿之时,邓小平就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这充分展现了这位设计者对于经济激励挤出伦理关怀的警觉,以及不同于“为小人立法”的现实智慧。若我们再能带上孔子关于“道之以德,其之以礼”的思考,也许,在21世纪初的现在,我们能够更靠近适合于当代中国经济治理的善政之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简单阐释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良性对话的框架,更多理论细节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就经济学理论排除伦理学的原因而言,除了前文从思想史角度的分析,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相应的分析思维(如局部分析、静态分析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就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融合而言,经济学如何嵌入伦理学之中而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对人性和制度结构的认知以及对经济分析逻辑的重新审视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如何处理量化研究和价值探讨的关系?不完全契约下的“不可能三角”以及激励相容的副作用在当代中国的经济治理中能有怎样的具体应用?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国内经济学者注意到经济问题的伦理维度,也让更多的哲学和社会学者看到经济学的伦理关怀。
| [1] | Bowles S. The moral economy: Why good incentives are no substitute for good citizen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 [2] | Fukuyama F.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1. |
| [3] | Hamlin A P. Ethics and economics[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6. |
| [4] | Hayek F A. The road to serfdom[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
| [5] | Kahn P W. Putting liberalism in its pla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 [6] | Robbins L.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2. |
| [7] | Sen A. On ethics and economic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
| [8] | Vickers D. Economics and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institutions, and policy[M]. London: Praeger, 1997. |
 2017, Vol. 19
2017, Vol.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