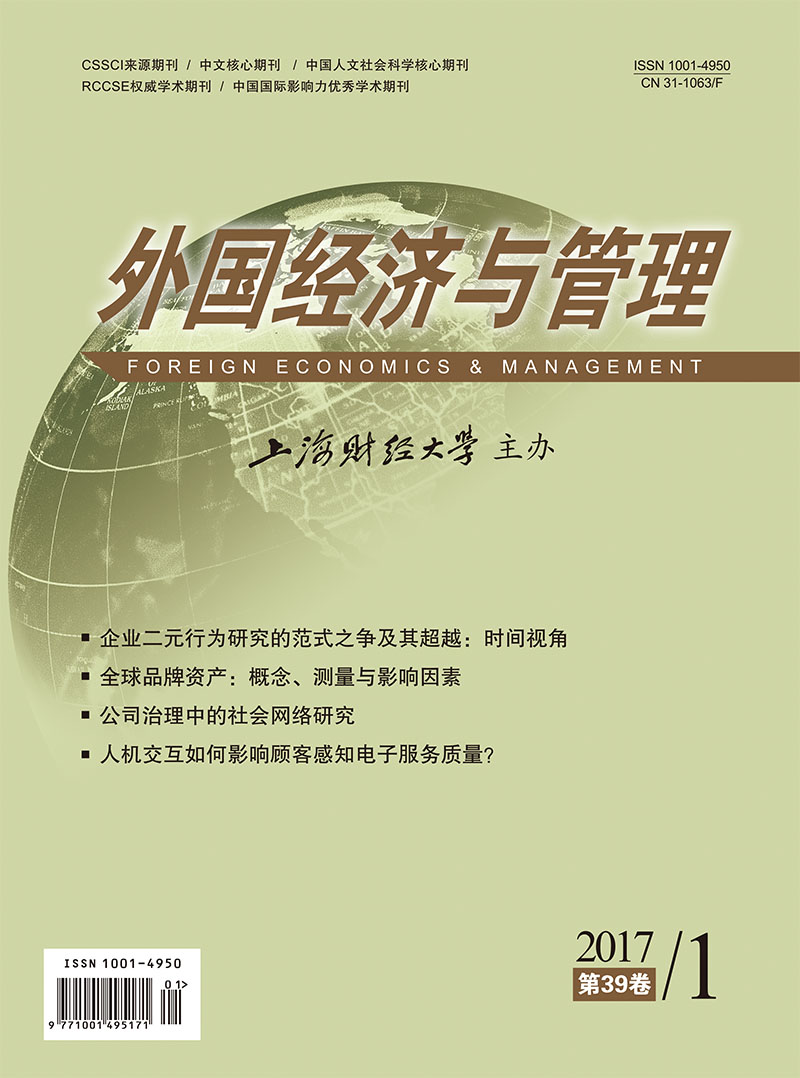2.华东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部,上海 200241
2.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近年来,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兴市场的全球品牌方兴未艾,引发世界瞩目(Kumar和Steenkamp,2013)。中国一些领先的跨国公司,如联想、中兴、华为等,它们的海外营业额已经超过了它们在国内市场的营业额(Einhorn,2012)。中国品牌华为和联想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登上著名的Interbrand“最具价值100全球品牌”榜单,成为新兴全球品牌的明星代表。事实上,全球品牌化是品牌战略的高级阶段(Keller,2013),全球性的品牌名称能够为产品带来额外的价值,即全球品牌资产。从理论上看,全球品牌化领域亟待研究的五大议题便包括全球品牌绩效问题,如品牌资产、市场份额等(Chabowski等,2013)。
基于上述时代与理论背景,明确全球品牌资产的概念内涵,厘清全球品牌资产的来源,梳理影响全球品牌资产的关键因素等,就显得尤其重要(何佳讯,2013)。对全球品牌资产的理解有助于企业把握消费者偏好全球品牌的价值关键,有助于跨国企业明确更值得关注的品牌资产,从而通过实施适应性的营销战略来显著改善消费者的品牌态度,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致、有效的品牌资产。因此,本文将通过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在总结现有文献关于全球品牌资产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辨明应重点关注的界定方式,并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全球品牌资产的测量方式、具体维度及影响因素展开述评,最后展望未来研究方向。
二、 全球品牌资产的概念内涵全球品牌化(global branding)是品牌发展的高级阶段,而全球品牌(global brand)则代表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价值(Shocker等,1994;何佳讯,2013)。然而,现有文献对全球品牌概念的界定并不一致(Özsomer和Altaras,2008;Dimofte等,2008)。因此,来源于全球品牌概念的“全球品牌资产”就成为需要厘清的重要概念。
事实上,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全球品牌具有不同于一般品牌的特殊价值,并将这种价值称作“全球品牌资产”(global brand equity,GBE)(Hsieh,2004;Torres等,2012)、“全球品牌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s of global brands,PVGB)(Alden等,2013)等。由于品牌形象是品牌资产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识别消费者关于品牌的强烈、独特且积极的联想则是品牌资产测量的关键(Keller,1993),因此也有学者使用“全球品牌形象”(global brand image)(Roth,1992;Park和Rabolt,2009)、“全球品牌联想”(global brand association)(Dimofte等,2010)或“品牌全球性效应”(brand globality effect)(Dimofte等,2008)等称谓来描述全球品牌的价值作用。与此同时,还有学者着重探究了消费者偏好或购买全球品牌的原因,即全球品牌资产的来源,并将其称作“全球品牌维度”(dimensions of global brand)(Holt等,2004)。
本文统一使用“全球品牌资产”的称谓。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回顾,我们把学者们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归纳为两类。下面,首先介绍这两类对全球品牌资产的界定,然后再运用品牌价值链模型阐述全球品牌资产与全球品牌价值的关系。
(一) 对全球品牌资产的界定1.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
以营销标准化的思路来看,全球品牌是指在其大多数目标市场中使用相似的品牌名称、定位战略及营销组合的品牌(Özsomer和Altaras,2008)。标准化的营销活动(如品牌形象战略、广告传播内容、沟通媒介选择等)能使企业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得更高的利润(Levitt,1983),由此塑造的一致且有效的品牌形象则能强化长期品牌资产(Roth,1995a;Park和Rabolt,2009),如建立清晰可靠的品牌形象、提升顾客忠诚等。然而,完全标准化是不可思议的,品牌的标准化存在程度上的区分(Hsieh,2002)。同时,企业是否选择标准化品牌战略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文化等市场特征因素(Roth,1995b)。即使是相同的品牌营销活动,其对不同国家消费者品牌形象感知和购买状况的提升作用也有可能因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不同(Roth,1995a;Hsieh,2004;Park和Rabolt,2009)。
从这一角度理解,某一品牌的全球品牌资产高低与其在不同国家的标准化程度有关,对其的界定应着重考量其地理表征。全球品牌资产指的是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一方面,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标准化程度越高,不同国家消费者对该品牌形象感知的差异程度越低,品牌强度就越大,品牌拥有的全球品牌资产也就越高。Hsieh(2002)用“全球品牌形象感知的聚合程度”(the degree of cohesiveness)来对品牌的全球化程度进行描绘,同时证明了该概念与品牌认知之间的正向关系,而后者正是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由于不同市场上的品牌资产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全球品牌资产应该是国家层面品牌资产汇总的结果(Motameni和Shahrokhi,1998;Hsieh,2004)。此时,国家层面品牌资产反映了品牌在不同国家内部价值来源的大小,而在国家层面上的汇总也可以考虑加入国家权重因子。这种界定方式的潜在前提是,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标准化,并且这种标准化对品牌有所裨益,但仍需意识到这种标准化品牌还具有地方性差异(Motameni和Shahrokhi,1998)。事实上,适度的地方性差异策略可以让全球品牌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最终也体现在全球品牌的价值中。
目前,采用这种界定方式的研究大多仅停留在构建全球品牌资产的测量方法阶段(如,Motameni和Shahrokhi,1998;Hsieh,2004)。主要原因在于,实证研究涉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数据搜集,操作难度与支出成本很高。然而,该界定下的全球品牌资产研究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通过测量品牌在不同国家的资产,跨国营销人员可以评估并比较品牌实力,进行标杆分析,以识别需要强化管理的特定国家或特定类型的品牌资产。
2.全球品牌特有的资产
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来看,品牌的全球性存在高低之分(Özsomer和Altaras,2008)。Steenkamp等(2003)提出了“品牌感知全球性”(perceived brand globalness,PBG)概念,以消费者感知到的同一品牌在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行销售的程度对其进行操作性测量。因此,全球品牌并不意味着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营销标准化。消费者可以通过媒体覆盖、口碑传播或旅行等方式接触到品牌在营销沟通中强调的“全球性”信息,如与全球消费者文化(global consumer culture,GCC)相关的象征符号,进而形成关于该品牌的全球性感知(Alden等,1999)。
事实上,消费者认为全球品牌拥有特别的信誉、价值和能力,对全球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可及性和认知度持有更强的偏好(Steenkamp等,2003)。因此,如果某一品牌的感知全球性较强,消费者自然会认为该品牌也具有超出其他品牌的优越性,即使其质量或价值在客观上未必更胜一筹,他们也倾向于选择全球品牌(Özsomer和Altaras,2008;Xie等,2015)。然而,感知全球性只是一种特殊的品牌联想(Özsomer,2012),在对品牌态度和购买偏好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信号作用(Özsomer和Altaras,2008;Özsomer,2012),具体的品牌属性才是解释市场行为的根本原因(Swoboda等,2012;Alden等,2013)。
基于这种思路,全球品牌资产揭示了品牌感知全球性发挥效用的价值机制。全球品牌整体上具备共同且独特的利益联想(如,感知质量、社会声望、全球神话、社会责任等),它们是驱动不同国家消费者评价和购买全球品牌的重要原因(Holt等,2004),即全球品牌资产的来源(Keller,1993)。相较而言,在第一种界定下,相关研究侧重探索的是“如何在不同国家建立一致、有效的品牌资产”(如,Hsieh,2004),而在第二种界定下,相关研究所聚焦的则是“全球品牌特有的资产如何影响消费者态度”(如,Steenkamp等,2003),但两种界定并不矛盾。第二种界定下的全球品牌资产在本质上仍是构成品牌形象的重要联想(Dimofte等,2010),同样应具备跨越地理维度和时间维度的一致性(Aaker和Joachimsthaler,1999),从而体现了第一种界定的内涵。
第二种界定方式是近年来全球品牌化领域关注的重点。学者们或研究全球品牌共通且独有的资产应该具备哪些维度(如,Holt等,2004),或探析全球品牌资产在品牌感知全球性与消费者态度间发挥的中介机制(如,Steenkamp等,2003),但极少基于跨国背景检视该视角下全球品牌资产结构及效应的一致性。在营销实践中,相关研究结论则能帮助全球品牌经理们明确需要重点进行管理的品牌资产维度,为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战略提供参考。
(二) 全球品牌资产在品牌价值链上的表征基于以上论述,可以从整合视角对全球品牌资产进行定义:全球品牌在国家层面开展的营销活动产生它在各个国家的品牌资产集合(第一类全球品牌资产),这种集合性的品牌资产又会形成超越国家层面的品牌资产,即全球品牌在非国家层面独有的品牌资产维度(第二类全球品牌资产),如感知品牌全球性、全球品牌真实性(global brand authenticity)、全球品牌声望等。它们共同影响品牌的市场业绩和股东价值,形成全球品牌价值链,表明全球品牌价值的来龙去脉(参见图 1)。它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品牌价值链(Keller,2013)的拓展和深化。

|
| 图 1 全球品牌资产的两种概念界定在品牌价值链上的表征 |
首先,全球品牌的价值始于营销人员在不同国家内部进行的营销活动投资。营销人员基于不同国家的特征(如,国家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定相应的营销方案(标准化、当地化或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塑造全球品牌在不同国家的形象(一致性或差异性)。即使某个品牌希望采取全球消费者文化定位战略(global consumer culture positioning,GCCP),相同的品牌意涵在不同国家或文化体的成员看来也可能拥有不同的含义(Hsieh,2004;Cayla和Arnould,2008;Akaka和Alden,2010)。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消费者对同一全球品牌所形成的顾客心智不尽相同,它们构成了品牌的区域性资产来源,而品牌的区域性顾客认知在各个国家相似或一致的部分及程度,则反映了第一类界定下全球品牌资产的来源。此时,比较衡量的基础是全球品牌在各个国家的资产。
其次,在顾客心智资源中,还有一部分属于超越具体品牌层面,为全球品牌所共有的独特属性和联想,如感知质量、社会声望、全球神话和社会责任等。这类联想代表着消费者偏好全球品牌的重要原因,也是全球品牌价值的主要来源(Holt等,2004)。即使不同的品牌联想对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重要程度有所差异(Shocker等,1994;Hsieh,2004),其维度及效应也拥有跨越国界的一致性(Aaker和Joachimsthaler,1999)。反过来看,不同国家的营销人员也应该基于这些特殊的品牌联想持续地构造具有创造性和差异性的营销项目,以提高全球品牌在品牌形象上的一致性和区别于一般品牌的独特性。因此,全球品牌作为独特整体而区别于其他品牌的共有认知特征,构成了第二类界定下全球品牌资产的来源。这里,比较衡量的基础则是全球品牌和非全球品牌各自所具备的整体性资产。
进一步地,全球品牌独具的顾客心智价值能形成优于一般品牌的市场业绩,即全球品牌资产的结果。例如,Torres等(2012)聚焦于研究跨国企业如何通过社会责任活动提升全球品牌资产。特别地,全球品牌的市场业绩并非是品牌的顾客心智价值的简单输出。顾客心智价值影响市场业绩的程度,还取决于一些市场因素,如竞争优势、渠道和其他中间商的支持、顾客的规模和情况等(Keller,2013)。事实上,实务界已开发出不同的指标体系以评估品牌的整体市场价值,如Interbrand、BrandZ等,为全球品牌提供了统一、可操作的价值衡量标准。
最后,全球品牌的市场价值会转化成金融市场上的财务价值(Dutordoir等,2015)。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品牌,其业务范围本身没有边界,而一旦在纳斯达克上市,则又会立即获得全球投资者的关注,取得极高的市场估值,体现出资本市场对全球品牌价值衡量的重要性。然而,这并不是完全必然的过程。事实上,基于消费者评价的EquiTrend品牌价值指标比基于财务绩效的Interbrand品牌绩效指标更能预测经济危机爆发时股票收益、股票价格波动和品牌风险系数等市场指标的趋势(Johansson等,2012)。同时,当Interbrand公司发布“最有价值100全球品牌”榜单后,上榜品牌的品牌价值变动可以正向预测品牌所在公司的超额股价收益率,但该关系还受到其他情境性因素的影响(Dutordoir等,2015)。
三、 全球品牌资产的测量方法对应于全球品牌资产在品牌价值链上的表征,全球品牌资产的测量方法也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即评估不同国家消费者关于全球品牌的所感所知再做汇总、从顾客心智角度评估全球品牌整体区别于一般品牌的特殊资产来源,以及通过评估全球品牌的市场业绩确定全球品牌资产。下面按照上述逻辑逐一进行介绍。
(一) 对品牌在全球范围的资产进行测量对品牌在全球范围的资产进行测量,思路通常有两种:第一,以不同国家消费者对全球品牌感知的标准化程度作为评价全球品牌资产的指标;第二,先计算品牌在各个国家的资产,再在全球层面上汇总品牌的全球资产。
在评估企业在不同区域市场上使用的品牌形象战略的一致程度时,Roth(1995b)使用了“品牌形象定制化/标准化”(brand image customization/standardization)称谓。首先,要求被访问的营销经理根据其所管辖品牌的实际状况,按照功能(functional)、社会(social)和感觉(sensory)三种基于利益的形象类型分配总共为100的分数,分数越高代表该类形象对品牌来说越重要。其次,计算每个品牌在不同市场上品牌形象得分的方差。此时,特定市场上品牌形象得分的比较对象是该品牌在所有市场上品牌形象得分的均值。计算所得方差越小,说明品牌形象越趋向标准化,反之越趋向定制化。
类似地,Hsieh(2002)使用涵盖20个国家的消费者关于53个汽车品牌利益联想评价的二手数据,建立了全球消费者在汽车品类上的品牌形象评价体系,得到各品牌在感觉形象(sensory image)、象征形象(symbolic image)、实用形象(utilitarian image)及经济形象(economic image)四个维度上的得分。进一步地,分别计算并汇总其他各国与品牌来源国在特定品牌各具体形象维度上得分差异的欧氏距离,将其命名为全球品牌形象的聚合程度,即全球范围内不同消费者对特定品牌形象感知的差异程度。特别地,此时用于比较的基准对象则是品牌来源国消费者对该品牌的形象感知。
在此基础上,Hsieh(2004)首次尝试测度全球品牌在每个国家的区域性资产,进而聚合成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资产。她将国家品牌资产(national brand equity,NBE)界定成可测量资产与不可测量资产两类,两者均先基于个体消费者进行测量,再进行国家层面上的汇总计算。前者反映各品牌利益联想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总体影响,同时考虑具体联想在不同市场中被感知到的消费者比例,将其作为权重因子。后者反映前者未能反映的品牌附加价值,在操作上体现为品牌虚拟变量对购买意愿的直接影响。就本质而言,可测量资产和不可测量资产分别体现了运用间接方法和直接方法对品牌资产进行测量的思路,即前者识别品牌资产的来源,而后者评估品牌知识的影响(Keller,2013)。进一步地,全球品牌资产是国家品牌资产乘上国家权重因子后在国家层面的汇总结果。国家权重因子则包括品牌识别度、品牌购买意愿及市场规模。
可以发现,在测度第一类界定下的全球品牌资产时,学者们倾向于以与品牌相关的利益联想代表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如,Hsieh,2002,2004;Park和Rabolt,2009)。然而,品牌形象总能体现品牌所在品类的具体特征,因此很难建立适用于多个品类的测量标准(Park和Srinivasan,1994;Hsieh和Li,2008)。与此同时,品牌形象是否是对品牌资产的完整表征,也值得商榷(如,Motameni和Shahrokhi,1998)。
(二) 对全球品牌特有的资产进行测量在测量全球品牌特有的资产时,往往采取间接方法识别和追踪消费者关于全球品牌的特殊利益联想,以评估全球品牌资产的来源。但是,目前专门探究全球品牌资产结构和维度的文献数量甚少,且在实际操作上存在分析层次上的差异。
综观现有文献,感知质量、全球神话、社会声望和社会责任是最受关注的全球品牌资产维度。表 1遵循Keller(1993)关于品牌利益(brand benefits)的划分标准,将与全球品牌相关的利益联想划分成功能、体验及象征三种类型。特别地,“本性”囊括了来源于全球品牌基本特征的联想属性(如,标准化、地理含义上的全球化等),但它们只是引发全球品牌资产联想的信号,本身并不影响消费者态度与品牌购买意愿(Steenkamp等,2003;Swoboda等,2012)。
| 分析 层次 |
研究者 | 全球品牌资产来源 | 实证基础 | |||||||
| 本性 | 功能 | 体验 | 象征 | |||||||
| 全球性 | 标准化 | 感知质量 | 相对价格 | 社会声望 | 情感表达 | 全球神话 | 社会责任 | |||
| 具体全球品牌 | Holt等(2004) | √ | √ | √ | 12个国家,6个品类,18个品牌 | |||||
| Madden等(2012) | √ | √ | 4个国家,1个品类,3个品牌 | |||||||
| Özsomer(2012) | √ | √ | 3个国家,3~8个品类,6~16个品牌 | |||||||
| Steenkamp等(2003) | √ | √ | √ | 2个国家,4个品类,8个品牌 | ||||||
| Swoboda等(2012) | √ | √ | √ | √ | 1个国家,1个品类,36个品牌 | |||||
| 全球品牌整体 | Alden等(2013) | √ | √ | 3个国家 | ||||||
| Dimofte等(2008) | √ | √ | √ | √ | √ | 1个国家 | ||||
| Dimofte等(2010) | √ | √ | √ | √ | 1个国家,3个种族 | |||||
| Özsomer和Altaras (2008) |
√ | √ | √ | √ | - | |||||
| Strizhakova等(2008) | √ | 4个国家,10个品类 | ||||||||
| Strizhakova等(2011) | √ | √ | 3个国家,10个品类 | |||||||
| Xie等(2015) | √ | √ | √ | 1个国家,1个品类 | ||||||
| 注:本表由本文作者整理。在整理过程中,按照文献中涉及的概念内涵和测项内容,将相关维度按照本文设定的框架做意义相符或相近的归集。 | ||||||||||
市场业绩反映了品牌资产的最终价值(Keller,2013)。因此,对全球品牌资产体现于市场业绩上的经济价值进行直接估算,是对全球品牌资产的最直观反映。这种做法多见于实务界。在具体操作时,并不区分全球品牌与一般品牌的差别,但从结果看,全球品牌往往获得更高的估值,反映为更强的品牌资产(又称作global BE)(如,Torres等,2012)。换言之,那些在品牌价值排行榜上排名越高的品牌,其全球品牌资产越强。目前,全球最受关注的品牌价值排行榜分别是Interbrand发布的“最佳100全球品牌”(Top 100 Best Global Brands)榜单和明略行(Millward Brown)推出的BrandZ“最有价值100全球品牌”(Top 100 Most Valuable Global Brands)榜单。
按照Interbrand的方法,品牌价值由财务绩效、品牌作用和品牌强度共同决定。在分析财务绩效时,将归集于品牌化产品的当前和未来收入减去运营成本与无形资产花费,即得到由品牌产生的经济利润。品牌作用指的是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产生的影响中除归功于价格、便利性、产品属性等因素外归功于品牌的部分。由品牌产生的经济利润与品牌作用相乘得到由品牌创造的收益。品牌强度则反映品牌维护持续的消费者需求(如,顾客忠诚、重复购买、顾客保留等)以及保持未来收益的能力,共分成十大因素,其参照标准是产业中的其他品牌或其他世界级品牌,在操作上可被转换为特定品牌的贴现率。按照该贴现率计算未来5年内由品牌创造的收益现值与第5年后的品牌残值,两者相加即为最终的品牌价值(Torres等,2012;何佳讯,2014)。从前面两个要素来看,Interbrand的方法蕴含了第二类全球品牌资产内涵界定。
明略行的方法同样需要分别计算品牌的无形收益、品牌在无形收益中的贡献以及可预测品牌未来收益的品牌乘数。特别地,在明略行的估值中,对品牌贡献的测度还会考虑地区差异,而对品牌乘数的计算则基于品牌在每个国家的短期成长指数(亦称作“品牌电压”,brand voltage),包括品牌未来提升市场份额的能力、所在品类的增长率和所在国家的增长率(何佳讯,2014)。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略行对全球品牌价值的衡量,是将各国市场上的品牌价值进行加总的结果(何佳讯,2014),体现出第一类全球品牌资产内涵界定。
事实上,Motameni和Shahrokhi(1998)曾经提出测量全球品牌资产的理论框架,在Interbrand估值法的基础上,还整合了第一、二类界定下对全球品牌资产的测量思路。具体地,全球品牌资产是品牌净收益与品牌乘数相乘的结果。前者是品牌化产品与非品牌化产品带来的收益之差,以国家为单位做数据搜集。后者则源于对品牌强度的计算:首先,将影响品牌强度的指标划分成顾客基础效能(如,品牌形象和品牌忠诚、品牌意识、品牌联想和感知质量)、竞争效能(如,品牌趋势、品牌支持、品牌保护和竞争强度)和全球效能(如,市场、分销、价格、监管等多种因素)三大类型。其次,在每个国家内部,对特定品牌在每一项指标上的表现进行评估,10分表示极占优势,–10分表示极不占优势。再次,为三大类型指标各分配总分为100的权重。仍然基于每个国家开展对管理层或消费者的调查,按照相关程度大小确定各类型指标下各条目因素的权重。然后,将品牌在各条目上的得分与对应权重相乘并汇总,将累计结果除以30①,得到品牌在该国家的品牌强度相对分数。最后,归集品牌在所有国家的品牌强度分数,得到其在全球层面的品牌强度指数。然而,要想得到品牌乘数,还应将品牌强度按照对品牌获取未来收入的信心水平进行贴现,贴现率以品类为单位进行计算,体现不同品类的特征。
①即三大类型下各条目得分与权重乘积之和的最大值。
相比较易知,Motameni和Shahrokhi(1998)的理论框架考虑了全球品牌在不同国家的区域性资产(第一类界定),与明略行的方法类似,并没有局限于Interbrand的方法仅考量的品牌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大小和持续程度(第二类界定),还将全球品牌资产的来源扩大到竞争效能和全球效能等市场环境或企业战略因素。同时,基于品类特征计算贴现率、以经济价值衡量全球品牌资产等做法亦为建立适用于多品类的测量标准、进行客观的横纵向比较提供了可能。然而,该理论方法的有效性尚未得到实证确认。
四、 全球品牌资产的影响因素拥有强大而有效的全球品牌资产的重要前提是,维持跨越地理范围的一致性和有效性(Hsieh,2002,2004;Park和Rabolt,2009)。然而,Fischer等(2010)提出了“品牌在品类中的相关性”(brand relevance in category,BRiC)这一新构念,认为品牌在顾客决策中的重要性因国家和品类的不同而不同,而BRiC的高低本身还受一些消费者异质性因素的权变影响,如性别、年龄等等。这说明,品牌资产的构成随国家不同而不同,其来源按照属性重要程度而有所变化(何佳讯,2013;Keller,2013)。因此,无论是品牌在不同国家的区域性资产(第一类界定),还是全球品牌特有的利益联想(第二类界定),都受到国家、消费者及品牌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何佳讯,2013)。基于现有文献,下面分别就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和品牌来源国进行论述。
(一) 经济发展水平按照Hsieh(2002)的研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中的消费者,对同一品牌的形象感知趋向一致。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是干扰全球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致品牌资产的因素之一,体现出第一类界定的内涵。事实上,Dimofte等(2010)发现,当评价针对全球品牌抽取出的各类利益联想时,代表美国少数族群的非裔和西班牙裔消费者确实给予了比代表美国主流消费者的高加索人更高的评价。延伸到第二类界定下的全球品牌资产维度,经济发展水平还影响它们对于不同国家消费者的重要程度。对于一些特定的全球品牌资产维度,它们是否稳定地存在于各个国家,甚至也值得深入研究。下面分别展开讨论。
首先,Holt等(2004)研究指出,质量信号对消费者的全球品牌偏好的变异解释程度高达44%,说明质量是全球品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以发达市场消费者为调查对象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Dimofte等(2008)将全球品牌作为整体概念进行研究,针对美国消费者的开放式问卷调查及内容分析结果显示,“质量”被提及的比例仅占5.4%。他们认为,品牌强度是引发质量联想的主要原因。在以具体全球品牌为研究对象时,消费者之所以会报告高质量联想,是因为这些品牌本身就拥有很高的品牌资产,而并非由品牌全球性所导致。类似地,Schuiling和Kapferer(2004)使用Young & Rubicam在欧洲市场上的品牌数据研究发现,在成熟市场上,本土品牌比全球品牌拥有更高的亲和度和质量评价。
其次,针对全球神话,Strizhakova等(2011)基于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比较了感知质量和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对消费者对全球品牌实际购买情况的影响。其中,自我认同的意涵与全球神话相近,但两者并不等同(Xie等,2015)。当评估品牌化产品重要性时,发达国家消费者对全球品牌的实际购买比例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品牌作为质量信号的作用,而在新兴市场,消费者同时出于将品牌作为质量信号和自我认同信号的考虑而购买全球品牌。换言之,全球神话更能促使新兴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全球品牌。
此外,虽然诸多学者曾经直接将社会声望作为感知品牌全球性影响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的中介变量(如,Özsomer,2012;Swoboda等,2012),但对全球品牌资产进行直接测量的相关研究中却没有单独出现这一维度(如,Holt等,2004;Dimofte等,2008)。事实上,当Steenkamp等(2003)考察社会声望对品牌购买可能性的促进作用时,他们只在韩国样本中检验到了两者间的显著关系,而在美国样本中该效应并不显著存在。这也说明,在考量社会声望给全球品牌带来的附加价值时,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
最后,针对社会责任,Strizhakova和Coulter(2013)发现,高物质主义的消费者往往给予全球公司(品牌)在环境责任上较高的评价,但两者关系又受消费者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消费者的全球/本土认同程度的共同影响。
(二) 文化价值观文化是“个体看待现象时使用的透镜”。也就是说,文化决定了个体如何感知并理解现象,为人类活动绘制了基本蓝图,指定了社会及生产活动的最初坐标,可以解释与之相关的行为和事物(Craig和Douglas,2006)。事实上,价值观是跨文化研究最常选择的构念(Smith等,2006)。在实际操作时,按照所选量表的不同,既可基于个体层面测量,又可基于国家层面测量。在国家层面,往往采用Hofstede(2001)的五维度价值观框架。在个体层面,主要采用Schwartz和Boehnke(2004)提出的11维度框架。此外,自我建构(self-construal)也可作为消费者个体层面的文化表征,可进一步细分成相依型自我(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和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Triandis,1989;Wong和Ahuvia,1998)。
在探究文化价值观对企业品牌战略的影响时,常依照的是Hofstede(2001)对文化的划分标准。具体地,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体主义在全球品牌形象战略(功能形象、社会形象与感觉形象)与产品绩效的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Roth,1995a);而当市场间文化差异(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体主义)较大时,营销经理们更可能采用定制化全球品牌形象战略,以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反之则采用标准化全球品牌形象战略(Roth,1995b)。这些结论表明,文化价值观是阻碍品牌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一致形象或资产(第一类界定)的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在试图开启品牌全球化进程时,需要依据东道国市场的文化特征来调整自身的品牌战略。
从消费者感知的角度,文化价值观在消费者评价品牌具体属性的过程中发挥着调节作用,佐证了前文关于全球品牌资产难以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论断(第一类界定)。在国家层面,Eisingerich和Rubera(2010)针对同一家居零售品牌在中英两国展开调查,发现在个体主义、短期取向和低权力距离的国家(英国),品牌创新性和品牌-自我相关性对品牌承诺的影响更大,而在集体主义、长期取向和高权力距离的国家(中国),品牌顾客取向和社会责任对品牌承诺的影响更大。但他们仅基于国别比较了效应值,并未切实检验价值观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地,Erdem等(2006)利用多国跨品类集合数据证明,品牌可靠性对品牌选择的促进作用在集体主义消费者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可靠品牌意味着高质量和更多价值;而该作用受到不确定性规避的正向调节,因为可靠品牌的感知风险和信息成本更低。在个体层面,Park和Rabolt(2009)则使用Schwartz(1994)开发的量表对美韩消费者的文化价值观分别进行了描绘。研究显示,两国消费者关于同一全球品牌(Polo)的形象感知差异源于其文化价值观的不同,而这种不同是通过消费价值观的差异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美国消费者认为Polo的品牌形象更趋于时尚、文雅,其消费价值观更注重情境因素和享乐因素,其文化价值观更偏重于平等主义、情感自主性、智力自主性及和谐等。而韩国消费者对上述要素的评价偏低,且更注重等级制度方面。
具体到那些全球品牌共通且特殊的资产(第二类界定),现有研究虽意识到文化价值观对其可能存在一定影响,但鲜有以此为主题的实证考察。例如,Madden等(2012)基于阿根廷、中国、西班牙和美国四国消费者的研究发现,关于三大汽车品牌的感知质量和社会责任评价是否受到晕轮效应的影响,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他们以Hofstede(2001)提出的五维度框架作为对文化价值观的表征,认为文化因素是上述差异产生的根源。具体地,阿根廷和西班牙在不确定性规避上的得分更高,因此两国消费者更倾向于基于具体的品牌特征而非基于品牌整体或其他特征的溢出印象给予评价。又如,在Özsomer和Altaras(2008)提出的研究命题中,自我建构可能调节着感知品牌全球性与品牌可靠性之间的关系:相对于高独立型自我的消费者,对于高相依型自我的消费者来说,感知品牌全球性对品牌可靠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而相对于高相依型自我的消费者,对于高独立型自我的消费者来说,全球品牌真实性对品牌可靠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然而,这两项研究都没有就其提出的命题开展实证检验。
(三) 品牌来源国目前,现有文献基本上将全球品牌的来源国做国外/本土或发达市场/新兴市场两种类型的划分。在具体研究上,则基本只限定在一个国家内展开调研,单独探讨来源国变量是如何调节消费者对不同全球品牌资产维度的评价与消费者的品牌态度或行为意愿之间的关系的,即第二类界定下的全球品牌资产。
首先,感知品牌全球性对消费者态度的影响机制因品牌来源国(外国VS本土)的区别而有所不同,具体的全球品牌资产维度可以解释这种差异,但差异内容仍因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方面,对于新兴市场的消费者来说,外国全球品牌所具有的功能价值和心理价值对消费者的态度和购买意愿具有同等重要的提升作用,而本土全球品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心理价值上。Swoboda等(2012)基于中国市场研究了感知品牌全球性对零售商品牌(外国VS本土)光顾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相较于本土零售品牌,感知品牌全球性对零售商光顾意愿的促进效应在外国零售品牌中体现程度更高。引入感知价值的中介机制后则发现,对于中国消费者,当品牌来源于外国时,感知品牌全球性对光顾意愿的正向作用同时需经由功能价值和心理价值的中介传导,且效应值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但本土品牌经由感知价值对行为意愿的促进作用则更多体现于心理价值的中介作用。
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市场的消费者而言,外国全球品牌在全球神话等心理价值上的作用更大,而本土全球品牌则因其更高的功能价值而引发积极态度。Riefler(2012)在奥地利开展的研究指出,当评价源于外国的全球品牌时,消费者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态度(globalization attitude,GA)直接正向影响全球品牌态度,而消费者的全球消费取向(global consumption orientation,GCO)对全球品牌态度的提升作用则需经过全球品牌评价(质量、形象和性价比)的中介传导;而当评价源于本国的全球品牌时,虽然全球化态度通过全球品牌评价对全球品牌态度产生正向的间接影响,但是消费者的全球消费取向则会直接正向影响品牌态度。此时,品牌全球性主要起到质量信号的作用。换句话说,除了对具体品牌属性的评估,发达市场消费者对本国品牌的积极态度还直接源于对这类品牌质量的认可,而对外国品牌的积极态度则受益于它们的“外来光环”(foreignness)。
其次,现实发展趋势促使学者们转向对新兴市场全球品牌和发达市场全球品牌差异的思考。在传统意义上,全球品牌大多源自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全球品牌开始崭露头角,如中国的华为、海尔、联想,印度的Tata汽车等。然而,从现实角度来看,西方消费者对以中国品牌为代表的新兴全球品牌的熟悉、接受程度以及态度和评价仍然不高(Kumar和Steenkamp,2013)。对于这些新兴的全球品牌而言,全球品牌资产带来的正向效应仍面临着发展中国家负面原产国联想的威胁(郭晓凌等,2014)。基于这样的背景,Guo(2013)初步探究了消费者具体特征对全球品牌资产评价的影响如何受品牌来源国的调节。虽然该研究选取的结果变量是全球品牌态度,但采取的是相对测量方式,就发达市场全球品牌和新兴市场全球品牌在感知质量、社会声望、创新程度、社会责任及吸引力等方面的差异对消费者(中国和印度)发问,如“发达市场全球品牌比新兴市场全球品牌拥有更高的质量”“发达市场全球品牌比新兴市场全球品牌的创新程度更高”等,实则是相对全球品牌资产的概念。基本结论显示,与发展中国家全球品牌相比,全球消费取向和全球认同对发达国家全球品牌态度的正向效应以及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对发达国家全球品牌态度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另外,消费者民族中心主义在全球消费取向和全球认同的正向效应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换言之,对于新兴市场的消费者而言,发达国家品牌的“全球性”光环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品牌。
五、 未来研究展望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回顾,首次提出全球品牌资产的两类界定,即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资产和全球品牌特有的资产。随后,本文从整合视角对全球品牌资产这一构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同时调整了Keller(2013)提出的品牌价值链模型,以进一步表征全球品牌资产与全球品牌价值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全球品牌资产对应的三种测量方式,即汇总品牌在不同国家内的顾客心智、识别全球品牌特有的顾客心智资源,以及衡量全球品牌的市场经济价值。最后,本文从国家、消费者和品牌三个角度,分别提取并阐述了影响全球品牌资产评价或效应的可能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价值观和品牌来源国。总体上,以全球品牌资产为主题的研究虽已累积了一定的成果,但实证探讨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进一步探究不同界定下的两类全球品牌资产的相互联系与影响关系。本文首次就全球品牌资产归纳总结出两大取向的概念内涵,并基于品牌价值链发展出关于全球品牌资产的整合性模型。然而,现有研究甚少涉及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两类全球品牌资产之间的动态关系。例如,企业在多大地理范围或目标市场、投入多大规模的营销投资、取得何种水平的品牌联想“相对”一致程度(第一类界定),才能达成塑造消费者感知到的品牌的“全球性”光环(第二类界定)的最终目标。又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消费者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进行跨国旅行、登录他国网站、收看全球视讯(Alden等,2006),也就更有可能对同一品牌在不同国家的定位和传播内容拥有越来越深入的了解(第一类界定)。那么,那些超越国家层面的全球品牌所独具的品牌资产(第二类界定)是否反过来也会促进企业在各个国家的品牌创建和经营活动?同时,这种反馈效应是否还存在某些边界条件?
其次,可以尝试将对全球品牌资产的研究和探讨拓展到市场业绩或股东价值上去。目前的全球品牌资产研究基本都遵从Keller(1993)提出的“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框架,从品牌的财务价值角度(Kapferer,2012)对全球品牌资产所进行的探讨,目前尚处于空白阶段。事实上,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市场业绩与基于投资者或股东的品牌资产是紧密相连的。一方面,品牌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消费者认可和市场销售业绩良好的信息能够向投资者传达利好信号,也就是说,基于顾客的全球品牌资产能够影响市场业绩,再影响基于投资者或股东的品牌资产。但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新兴市场中的品牌,这种关系有可能是负向的。例如,尽管消费者普遍对淘宝等购物平台持有“低价”“质次”等不利联想,但在2015年“双十一”促销大战中,阿里巴巴旗下各平台总交易额达到912亿元,而当天阿里巴巴的股价却不升反跌,跌幅一度超过3%,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市场业绩和股东价值彼此之间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目前,来自中国企业的真正的全球品牌还很少,但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已达到近200家。品牌在全球资本市场中的表现,反过来会影响顾客对品牌的态度和行为,即存在基于投资者或股东的品牌资产对市场业绩和基于顾客的全球品牌资产的逆向影响关系。当在品牌价值链上表征全球品牌资产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品牌价值有可能存在双向互动的影响机制。
再次,对全球品牌资产维度提升品牌价值的机制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目前,实证研究关注的仅仅是全球品牌资产维度在感知品牌全球性与行为变量间的中介作用(如,Steenkamp等,2003;Özsomer,2012),以具体资产维度为核心变量的研究数量极少。例如,各项全球品牌资产维度对品牌态度和购买意愿的影响过程是否存在中介机制?哪些消费者特征会促使消费者看重全球品牌在特定维度上的绩效状况?事实上,Xie等(2015)的研究考察了品牌信任和品牌情感在感知质量、社会声望及品牌身份表达等全球品牌资产维度与行为变量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特别地,从消费者文化理论的角度,全球品牌具备的文化资本让全球品牌具备了真实性(Özsomer和Altaras,2008)。那么,品牌真实性在全球品牌资产效应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相关结论对于我们理解全球品牌资产发挥效应的原因,强化全球品牌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着重分析来自新兴市场的品牌和来自发达市场的品牌在全球品牌资产维度及其效应上的差异,为具体的全球品牌资产管理提供基础性诊断信息,使得营销人员能够明确和妥善利用各自品牌的独特资产优势。现有文献虽然已经表明,从消费者评价来看,新兴市场的全球品牌所具备的全球品牌资产在整体上要弱于发达市场的全球品牌(如,Guo,2013;Kumar和Steenkamp,2013),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全球品牌(VS发达市场全球品牌)在各项全球品牌资产上所获得的消费者评价完全处于劣势,也不表明具体维度的全球品牌资产对消费者态度的总体促进作用总是在发达市场全球品牌(VS新兴市场全球品牌)中体现得更强。一些问题值得未来探究,例如,感知质量对品牌态度的整体影响是否在新兴市场全球品牌(VS发达市场全球品牌)中体现得更强?相对应地,全球神话对品牌态度的整体影响是否在发达市场全球品牌(VS新兴市场全球品牌)中体现得更强?事实上,进行评价的消费者所处的是新兴市场还是发达市场,也会对上述机制产生差异化影响。上述种种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
| [1] | 何佳讯. 全球品牌化研究回顾:构念、脉络与进展[J].营销科学学报,2013(4) : 1–19. |
| [2] | Aaker D A, Joachimsthaler E. The lure of global branding[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9,77(6) : 137–144. |
| [3] | Alden D L, Kelley J B, Riefler P, et al. The effect of global company animosity on global brand attitudes in emerging and developed markets:Does perceived value matter?[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13,21(2) : 17–38. |
| [4] | Alden D L, Steenkamp J B E M, Batra R. Brand positioning through advertising in Asia,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The role of global consumer culture[J].Journal of Marketing,1999,63(1) : 75–87. |
| [5] | Alden D L, Steenkamp J B E M, Batra R. Consumer attitudes toward marketplace globalization:Structur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2006,23(3) : 227–239. |
| [6] | Chabowski B R, Samiee S, Hult G T M.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global branding literature and a research agend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3,44(6) : 622–634. |
| [7] | Dimofte C V, Johansson J K, Bagozzi R P. Global brands in the United States:How consumer ethnicity mediates the global brand effec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10,18(3) : 81–106. |
| [8] | Dimofte C V, Johansson J K, Ronkainen I A.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reactions of U. S. consumers to global brand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8,16(4) : 113–135. |
| [9] | Dutordoir M, Verbeeten F H M, De Beijer D. Stock price reactions to brand value announcements:Magnitude and moderato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2015,32(1) : 34–47. |
| [10] | Eisingerich A B, Rubera G. Drivers of brand commitment:A cross-nation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10,18(2) : 64–79. |
| [11] | Erdem T, Swait J, Valenzuela A. Brands as signals:A cross-country validation study[J].Journal of Marketing,2006,70(1) : 34–49. |
| [12] | Fischer M, Völckner F, Sattler H. How important are brands? A cross-category, cross-country study[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10,47(5) : 823–839. |
| [13] | Guo X L. Living in a global world:Influence of consumer global orientation on attitudes toward global brands from developed versus emerg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13,21(1) : 1–22. |
| [14] |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
| [15] | Holt D B, Quelch J A, Taylor E L. How global brands compet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4,82(9) : 68–75. |
| [16] | Hsieh M H. Identifying brand image dimensionality and measuring the degree of brand globalization:A cross-national stud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2,10(2) : 46–67. |
| [17] | Hsieh M H. Measuring global brand equity using cross-national survey dat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4,12(2) : 28–57. |
| [18] | Johansson J K, Dimofte C V, Mazvancheryl S K. The performance of global brands in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A test of two brand value measur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2012,29(3) : 235–245. |
| [19] | Kapferer J N. The new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Advanced insights and strategic thinking[M]. London: Kogan Page, 2012 . |
| [20] | Keller K L. Conceptualiz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J].Journal of Marketing,1993,57(1) : 1–22. |
| [21] | Keller K L.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Build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brand equity[M].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13 . |
| [22] | Kumar N, Steenkamp J B E M. Brand breakout:How emerging market brands will go global[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
| [23] | Madden T J, Roth M S, Dillon W R. Global product qua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ceptions:A cross-nationalstudy of halo effect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12,20(1) : 42–57. |
| [24] | Motameni R, Shahrokhi M. Brand equity valuation:A global perspective[J].Journal of Product & Brand Management,1998,7(4) : 275–290. |
| [25] | ÖzsomerA. The interplay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brands:A closer look at perceived brand globalness and local iconnes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12,20(2) : 72–95. |
| [26] | ÖzsomerA, AltarasS. Global brand purchase likelihood:A critical synthesis and an integrated conceptual framework[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08,16(4) : 1–28. |
| [27] | Park H J, Rabolt N J. Cultural value, consumption value, and global brand image:A cross-national study[J].Psychology & Marketing,2009,26(8) : 714–735. |
| [28] | Riefler P. Why consumers do (not) like global brands:The role of globalization attitude, GCO and global brand origi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2012,29(1) : 25–34. |
| [29] | Roth M S. The effects of culture and socioeconomics on the performance of global brand image strategie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5a,32(5) : 163–175. |
| [30] | Roth M S. Effects of global market conditions on brand image customization and brand performance[J].Journal of Advertising,1995b,24(4) : 55–75. |
| [31] | Schwartz S H. Beyond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New cultural dimensions of values[A]. Kim U, Triandis H C, Kâğitçibaşi C, et al (Ed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C]. Thousand Oaks, CA:SAGE Publications, 1994:85-119. |
| [32] | Shocker A D, Srivastava R K, RuekertR 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acing brand management: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4,31(2) : 149–158. |
| [33] | Smith P B, Bond M H, Kagitcibasi C. Understanding social psychology across cultures:Living and working in a changing world[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6 . |
| [34] | Steenkamp J B E M, Batra R, Alden D L. How perceived brand globalness creates brand valu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3,34(1) : 53–65. |
| [35] | Strizhakova Y, Coulter R A, Price L L. Branding in a global marketplace: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quality and self-identity brand signal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2011,28(4) : 342–351. |
| [36] | Strizhakova Y, Coulter R A. The "green" side of materialism in emerging BRIC and developed markets:The moderating role of global cultural identit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2013,30(1) : 69–82. |
| [37] | Swoboda B, Pennemann K, Taube M.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brand globalness and perceived brand localness in China:Empirical evidence on Western, Asian, and domestic retailer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12,20(4) : 72–95. |
| [38] | Torres A, Bijmolt T H A, Tribó J A, et al. Generating global brand equity through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key stakehold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2012,29(1) : 13–24. |
| [39] | Triandis H C. The self and social behavior in differing cultural contexts[J].Psychological Review,1989,96(3) : 506–520. |
| [40] | Xie Y, Batra R, Peng S Q. An extended model of preference formation between global and local brands:The roles of identity expressiveness, trust, and affec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2015,23(1) : 50–71. |
 2017, Vol. 39
2017, Vol.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