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第48卷第11期
2. 广州大学 乡村振兴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 Institut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 China
一、引 言
进入21世纪以来,WTO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举步维艰,而双边或多边优惠贸易协定快速发展。中国紧随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将实施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s,以下简称FTA)战略作为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并且在党的十七大将FTA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在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五中全会、十九大等重要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和强调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要求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截至2021年11月30日,中国已签署19个FTA,涵盖26个国家或地区,其中16个FTA已经生效。当前FTA已经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①而且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背景下承担着缓解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要功能(冯帆等,2018;吕建兴等,2021a)。
虽然当前已有大量学者评估了FTA生效后的贸易效应(Baier和Bergstrand,2007;Larch等,2019),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分析FTA生效后整体关税减让的贸易效应。事实上,每个FTA生效后并不是所有产品的关税一次性地立即降到0,而是根据特定的目标分批次、分梯度逐步削减,而且部分产品不参与关税减让。为此,从整体层面将所有产品的关税减让视为同质的评估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那么,在当前中国加快构建FTA网络、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FTA中关税减让对进口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对进口的作用是否一样?当前针对部分产品设置不同的关税减让过渡期,那么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对进口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回答好上述问题,既可为科学评估FTA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提供现实证据,也可为未来在FTA中制定更为精准的贸易政策和贸易谈判提供更为坚实的科学依据。
为了科学评估FTA生效后关税减让对进口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147(国家/地区)×5224(产品)×17(年)的面板数据,根据双重差分法(DID)的估计策略,以没有参与FTA的“国家/地区—产品”为对照组,以参与FTA的“国家/地区—产品”为试验组,以FTA产品层面的关税减让生效前后为时间控制阀,通过对FTA关税减让生效前后以及是否参与FTA“国家/地区—产品”的差分来识别关税减让的净效果,并利用三重差分法(DDD)来识别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和不同过渡期对进口的影响。同时,本文基于产品层面来捕捉不同产品关税减让、关税减让过渡期以及原产地规则的异质性,并利用泊松伪极大似然(Poisson pseudo-maximum likelihood,以下简称PPML)高维固定效应估计技术来控制巨量的多向固定效应(出口地—时间、产品—时间、出口地—产品以及出口地—行业—时间固定效应)以及FTA贸易效应分析中必须面对的巨量“零值贸易”、异方差、FTA内生性以及多边贸易阻力等问题(Head和Mayer,2014;Yotov等,2016)。
本文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关税减让显著促进了进口,但由于遵守原产地规则引致的执行成本,只有关税减让幅度超过5%时进口促进效应才显著;随着关税减让幅度的增加,进口促进作用逐步增强,而且关税减让过渡期越长,进口促进作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此外,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和过渡期对不同属性产品的进口作用不同,这体现了不同进口战略的效果。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三篇,本文力争做到“取长补短”。Manchin和Pelkmans-Balaoing(2008)实证分析了东盟FTA关税减让幅度对贸易的影响,发现只有当关税减让幅度大于25%时,其对进口才有显著影响。Jean和Bureau(2016)实证分析了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发现关税减让幅度大于5%才显著促进出口。但这两篇文章均只关注产品层面不同关税减让幅度的差异,而忽视了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的差异。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体现了政府对特定产业的保护策略(吕建兴等,2021b),而且现实中大部分产品也是逐步减税(Tariff phase-out)的。因此,重视FTA间和产品间的异质性对于准确衡量FTA的贸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Besedes等(2020)基于产品层面的数据分析了NAFTA不同关税逐步减让对贸易的影响,发现关税逐步减让确实对进口有促进作用,但是这样的促进作用不是来自如Baier和Bergstrand(2007)所指出的来源于过渡期5年或10年产品关税减让的作用。该文从过渡期角度分析了不同降税模式对进口的影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FTA中关税减让与原产地规则密切相关,该文只考虑过渡期,而没有考虑关税减让幅度,为此该文有待进一步拓展。
同先前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在数据库建设上,本文从“国家/地区—产品—时间”层面构建了一个科学评估FTA贸易效应的三维面板数据库,为解决FTA贸易效应研究中的技术难题和系统评估FTA的贸易效应奠定数据基础。(2)在估计方法上,本文采用DID和DDD的估计策略来识别关税减让的进口效应,同时利用高维固定效应PPML估计技术来控制巨量的三向固定效应,以及合理处理“零值贸易”、FTA内生性和“多边贸易阻力”问题,使得估计结果更为可靠。(3)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关税减让幅度、关税减让过渡期以及不同过渡期不同关税减让幅度等角度实证分析关税减让对进口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更可靠,政策指导意义更强。
二、理论分析、研究假说与理论突破
(一)FTA贸易效应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当前关于FTA贸易效应的测度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成果,而且主要沿着更加精准测度的方向演进,大体可将其分为以下两种:(1)从国家层面测度FTA的贸易效应。由于当前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多个FTA,而FTA网络错综复杂且相互影响,为此仅评估单个FTA的贸易效应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偏差,为此当前部分学者基于国家总体层面展开多个FTA贸易效应的评估(Baier和Bergstrand,2007;Larch等,2019)。(2)从“国家/地区—产品”层面测度FTA的贸易效应。由于不同FTA不同产品间关税减让模式、原产地规则等设置存在巨大差异,而忽略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偏差,因此基于“国家/地区—产品”层面考察FTA的贸易效应成为最新研究趋势。例如,Urata和Okabe(2014)基于67个国家20个产品分析了FTA的贸易效应,Jean和Bureau(2016)基于74个国家农产品的数据分析了FTA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理论上,FTA生效后能否产生贸易效应与企业是否利用FTA密切相关。如果企业不利用FTA,那么FTA建立生效后的贸易效应可能不大。在FTA中,原产地规则是产品的“经济国籍”,企业想要享受关税减让的优惠待遇,则必须遵循相应的原产地规则。而在中间品贸易占2/3的全球贸易下,遵守原产地规则要求企业跟踪相应的产品信息,并且调整相应的生产和贸易策略,这会增加企业的执行成本。为此,只有企业利用FTA所获得的关税优惠大于遵守原产地规则而额外付出的执行成本,FTA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意味着只有关税减让达到一定幅度才可能对贸易有促进作用(Manchin和Pelkmans-Balaoing,2008;Jean和Bureau,2016)。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1:由于遵守原产地规则要付出额外的执行成本,因此只有关税减让达到一定幅度才可能产生促进贸易的作用。
FTA建立的主要目标是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双边贸易,提高双边福利水平,其最优策略是FTA生效后双边立即全部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现实中大部分FTA的设置都是一个次优选择,也即大部分国家为了减缓大量进口对国内进口竞争型产业(特别是敏感产业)的冲击,通常会设置一定的关税减让过渡期,而且部分产品会成为关税减让的例外安排。Baier和Bergstrand(2007)研究发现,FTA生效后10年,双边贸易翻一番,因为当过渡期(10年)过后,这些产品开始降税,贸易效应才开始显现。但Besedes等(2020)基于多国多产品的数据检验了CUSFTA/NAFTA不同关税过渡期对贸易的影响,发现产品层面的关税逐步减让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来源于过渡期(5—10年)这些产品的进口增长。总体上,对于FTA生效后但还没开始执行关税减让的产品,企业利用FTA的积极性不高;而当关税减让过渡期到期后,而且企业利用FTA获得的关税优惠幅度大于支出的执行成本时,企业愿意利用FTA,那么FTA带来的贸易效应逐步显现。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2:FTA生效后,随着关税减让过渡期到期,FTA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逐渐显现。
(二)FTA贸易效应测度的研究困难
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对测度FTA贸易效应做了大量工作,但正如Head和Mayer(2014)所指出的,这些贸易效应测度结果存在很大差异且不稳健,而如何处理FTA的内生性、异质性和“多边贸易阻力”问题可能是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对于FTA内生性和“多边贸易阻力”问题的认识和处理,当前学者们基本已形成共识,即双边国家建立FTA不是外生的,而可能受到双边贸易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如两国贸易量越大、经济联系越紧密,越容易形成FTA(Baier和Bergstrand,2007),而且双边贸易流量同时受到来源国和目的国价格的影响(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当前处理内生性问题的主流方法是构建面板数据,控制国家间、国家—产品间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可观测的因素(Baier和Bergstrand,2007;Yotov等,2016)。而处理“多边贸易阻力”问题主要是通过控制国家—时间和产品—时间固定效应,进而控制不同出口国不可观测因素(如政策、供给、汇率、产品质量变化等)的影响(Head和Mayer,2014;Yotov等,2016)。
关于异质性,主要表现为FTA之间以及产品之间的异质性。从国内外相关研究来看,当前已有较多学者关注到FTA的异质性问题(Baier等,2018)和FTA滞后效应问题(Baier和Bergstrand,2007;Baier等,2014),但是少有文献关注产品层面异质性问题。其中,关于FTA之间的异质性,先前大量文献研究多个FTA效应时,只是通过设置0—1虚拟变量来度量某个国家是否参与FTA,这种处理方式将不同FTA对贸易的影响视为等同的。但现实中不同FTA关于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具体规定差异很大,深度也不同(韩剑和王灿,2019),显然其对贸易的影响也不同。就中国的FTA而言,不同FTA生效后关税减让幅度和关税减让过渡期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如中国—东盟FTA的平均关税减让幅度达8.43%,而中国—韩国FTA的平均关税减让幅度仅为2.14%;再如中国—冰岛FTA生效后关税立即降为0的产品占94.20%,而中国—韩国FTA仅占15.64%。而且大多数FTA关税减让是逐步进行的,因此设置国家层面的虚拟变量无法捕捉这些细微变化引致的贸易效应(Urata和Okabe,2014)。而且,这种异质性在产品层面的表现更为明显。从关税减让幅度来看,中国FTA中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减让幅度最高(9.30%),而中间品最低(5.97%),具体细分优惠幅度的差异更明显。同时,产品异质性在不同过渡期的表现也非常明显,关税立即降为0的关税减让幅度为5.28%,但过渡期(2—5年)平均关税减让幅度达7.18%。可见,忽略产品异质性问题同样可能会造成较大的估计偏差。
三、中国FTA关税减让的基本特征
随着不同FTA的逐渐生效,FTA优惠关税与最惠国待遇(MFN)关税的差异逐渐体现出来。从2006—2018年平均MFN关税和平均FTA优惠关税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②十几年来中国平均MFN关税呈小幅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10.30%下降至2018年的9.88%。同期,随着不同FTA不同产品关税减让的逐渐生效,中国平均FTA优惠关税呈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3.72%下降至2018年的0.83%。由于FTA优惠关税下降幅度大于MFN关税,因此平均关税优惠幅度也呈扩大趋势,从2006年的6.58%上涨至2018年的9%。
根据不同产品的平均减让幅度和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关税优惠情况,③可以发现:(1)MFN关税较高的产品,平均关税减让幅度也比较大。例如,农产品的MFN关税达14.23%,相应关税减让幅度达9.30%,高于工业品的6.67%;战略品的MFN关税为18.27%,其关税减让幅度达11.77%,高于非战略品的5.36%。(2)总体而言,关税减让过渡期越长,关税减让幅度越大。例如,农产品关税减让幅度从立即降为0的6.21%上升至过渡期6年及以上的9.44%,同样中间品从4.87%上升至6.57%。(3)不同产品不同过渡期关税减让幅度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非战略品关税立即降为0的优惠幅度为4.73%,但战略品关税立即降为0的优惠幅度达13.30%,两者相差8.57%。不同产品属性不同过渡期关税减让幅度存在较大差异,说明评估FTA贸易效应时考虑产品的异质性以及不同产品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异质性非常重要。
根据不同FTA不同过渡期、不同减让幅度以及税目占比情况,④可以发现:(1)不同FTA平均关税减让幅度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总体上FTA生效时间越长,关税减让幅度越大。例如,最早签订生效的中国—东盟FTA关税减让幅度最大,而且2011年以前生效的FTA的关税减让幅度也明显大于2014年以来生效的FTA的关税减让幅度。(2)相同过渡期不同FTA的关税优惠存在一定差异。例如,无过渡期(关税立即降为0)优惠幅度最大的为中国—巴基斯坦FTA,而最小的为中国—新西兰FTA;2—5年过渡期关税减让幅度最大的为中国—东盟FTA,而最小的为中国—瑞士FTA;6年及以上过渡期关税减让幅度最大的为中国—新西兰FTA,而最小的为中国—瑞士FTA。当然上述特征与部分FTA生效时间较短有关系。(3)不同FTA不同过渡期的关税减让幅度呈现不同特征。例如,中国与东盟、智利等FTA的关税减让幅度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即关税立即降为0和6年及以上过渡期的关税减让幅度较小,而2—5年过渡期的关税减让幅度较大;而中国与巴基斯坦、冰岛等FTA的关税减让幅度则呈现逐渐减小的特征;中国—新西兰FTA的关税减让幅度却表现出逐渐增加的特征。(4)不同FTA不同过渡期关税减让覆盖的税目差异很大。例如,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冰岛等FTA税目占比呈逐渐减少特征,而中国与东盟、巴基斯坦等FTA税目占比却表现为逐渐增多的特征,中国与智利、新西兰等FTA税目占比呈现出“中间多两头少”的特征,中国—秘鲁FTA税目占比表现为先减少再增加的特征。
从上述不同FTA及其涉及的过渡期和关税减让幅度的基本特征可知,如果不采用最为细分的产品层面数据,那么就无法控制不同产品的关税减让幅度、关税减让过渡期以及原产地规则等方面的异质性,进而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差异较大和不稳健问题。
四、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1. FTA进口效应的计量估计式。为了识别关税减让对进口的影响,根据DID的估计策略,本文以没有参与FTA的“国家/地区—产品”为控制组,以参加FTA“国家/地区—产品”为试验组,以关税减让生效前后为时间控制阀,通过对关税减让生效前后以及是否参与FTA的双重差分来识别关税减让的净效果。基于PPML的估计技术,将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 $ impor{t_{ijpt}} = \exp (\alpha + \gamma ×tariff\_margi{n_{jpt}} + \delta× droo\_inde{x_{jpt}} + {I_{jt}} + {I_{pt}} + {I_{jp}}) + {\varepsilon _{ijpt}} $ | (1) |
其中,
借鉴Jean和Bureau(2016)处理方法,用
在FTA中,企业是否利用FTA进行贸易,主要取决于企业遵守原产地规则所支付的执行成本和享受关税减让优惠程度的比较。此外,由于FTA生效后关税减让和原产地规则对贸易的作用是叠加的,因此要准确估计关税减让效应,需要控制原产地规则的作用。借鉴Roh和Park(2014) 关于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roo_index)的构建原则,本文根据中国FTA原产地规则的搭配组合,将现有原产地规则整理为39类,并根据相应限制程度进行赋值,构建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⑥
2. 不同关税减让幅度的计量估计式。为了识别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对进口影响的差异,借鉴Manchin和Pelkmans-Balaoing(2008)的思路,本文将MFN关税与FTA优惠关税的差异划分为0%—5%、5%—10%、10%—15%、15%—20%和20%及以上5个虚拟变量(
| $ \begin{gathered} impor{t_{ijpt}} = \exp (\alpha + \sum\limits_{k = 1}^5 {{\lambda _k}tariff\_margi{n_{jpt}} \times differenc{e_k}} + \delta droo\_inde{x_{jpt}} \\ \begin{array}{*{20}{c}} {}&{}&{}&{\begin{array}{*{20}{c}} {}&{} \end{array}} \end{array} + {I_{jt}} + {I_{pt}} + {I_{jp}} + {I_{jst}}) + {\varepsilon _{ijpt}} \\ \end{gathered} $ | (2) |
其中,
3. 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的计量估计式。为了符合WTO/GATT关于建立FTA的要求,当前大多数FTA关税降为0的税目占比已经达到90%,但是从具体产品层面看,大多数产品的降税都是逐步实施的,也即不同产品关税减让是存在过渡期的,而且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体现了一定的保护策略。据此,本文设置3个虚拟变量(
| $ \begin{aligned} impor{t_{ijpt}} =& \exp (\alpha + \sum\limits_{m = 1}^3 {{\varphi _m}tariff\_margi{n_{jpt}} \times phas{e_m}} + \delta droo\_inde{x_{jpt}} +\\ & {I_{jt}} + {I_{pt}} + {I_{jp}} + {I_{jst}}) + {\varepsilon _{ijpt}} \end{aligned}$ | (3) |
其中,
4. 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不同减让幅度的计量估计式。最后,由于不同产品不同过渡期的关税减让幅度存在异质性,为了更为细致地捕捉和刻画这种异质性,本文在估计式(2)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
| $ \begin{aligned} impor{t_{ijpt}} = & \exp (\alpha + \sum\limits_{n = 1}^{15} {{\psi _n}tariff\_margi{n_{jpt}} \times differenc{e_k} \times phas{e_m}}\\&+ \delta droo\_inde{x_{jpt}} + {I_{jt}} + {I_{pt}} + {I_{jp}} + {I_{jst}}) + {\varepsilon _{ijpt}} \end{aligned} $ | (4) |
其中,
(二)数据库建立与处理
本文的数据结构是一个具有三个维度的面板数据。第一个维度是中国与贸易伙伴国/地区签署FTA的情况。截至2021年11月30日,中国已签署19个FTA。考虑到部分优惠贸易协定尚未生效以及生效时间较短等原因,本文主要考察中国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哥斯达黎加、秘鲁、瑞士、冰岛、澳大利亚和韩国签署并生效的11个FTA。同时,为了评估FTA中关税减让对贸易的影响,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了与中国具有贸易关系且没有签订FTA的136个国家/地区作为控制组。因此,本文研究对象共计147个国家/地区。第二个维度是细分的产品维度,由于不同产品的关税减让模式、原产地规则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为了考察这种异质性,本文从HS6位码的产品层面展开研究。基于HS2002年版本6位码计算,每年每个国家/地区有5 224个产品。第三个维度是时间维度。基于数据可得性及为了消除加入WTO对贸易的影响,本文研究期限为2002—2018年。
由于在FTA中,对于FTA生效后MFN关税已经为0以及MFN关税等于FTA优惠关税的情况,企业不会选择使用FTA,而会继续在MFN关税水平下进行贸易。据此,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剔除了MFN关税已经是0以及MFN关税等于FTA优惠关税的样本。
由于各个FTA生效时间不同,为了能够将不同HS版本的FTA纳入一个可比较分析框架,需要对不同HS版本进行集结。本文先将HS8位码产品统一归结为HS6位码,再根据联合国提供的HS对照表将不同HS版本的产品统一归结为HS2002版本。
本文关于HS6位码产品层面的原产地规则和关税减让模式的数据均来自FTA原始法律文本,资料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贸易额、MFN关税和FTA优惠关税数据来源于WITS数据库,贸易双方名义GDP、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双方距离、是否拥有共同边界数据来自CEPII基础数据库。⑦
五、估计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估计结果⑧
根据表1的结果可以发现:第一,FTA关税减让显著促进了进口,关税减让幅度引致的产品价格下降1%,进口增加6.03%。比较表1列(1)和列(6)的结果可以发现,列(1)单独控制出口国/地区、时间和产品固定效应,关税减让幅度(tariff_margin)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不符合预期;而列(6)则是根据Baier和Bergstrand(2007)等的建议,控制了出口国/地区—时间、产品—时间和出口国/地区—产品固定效应,此时关税减让幅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符合理论预期与现实情况。该对比结果表明,如果没有很好地处理FTA内生性、异质性和“多边贸易阻力”问题,那么模型估计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甚至产生相反的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 |
| import | import | import | ln(import) | ln(import+1) | import | |
| tariff_margin | −5.400**(2.310) | 2.160(1.903) | 5.944***(1.325) | 2.161***(0.517) | 0.918***(0.156) | 6.028***(1.264) |
| cons | −11.449**(5.584) | 13.274***(0.027) | 7.265*(3.751) | 3.947***(0.005) | 0.517***(0.001) | 13.411***(0.011) |
| droo_index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lngdp、lnpop | 控制 | 非控制 | 控制 | 非控制 | 非控制 | 非控制 |
| 出口地、产品、时间 FE | 控制 | 非控制 | 非控制 | 非控制 | 非控制 | 非控制 |
| 出口地×时间 FE | 非控制 | 控制 | 非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产品×时间 FE | 非控制 | 非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出口地×产品 FE | 非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N | 12 854 656 | 3 466 460 | 3 354 222 | 1 547 173 | 13 003 374 | 3 352 745 |
| Pseudo/Adj. R2 | 0.736 | 0.951 | 0.978 | 0.779a | 0.838a | 0.981 |
| 注:括号内为出口地×时间、产品(HS6位码)×时间和出口地×产品多向聚类的稳健标准误;a表示调整后的R2;*、**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 ||||||
第二,忽视产品层面和国家或地区层面的异质性,会造成有偏的估计结果。分别比较表1列(2)、列(3)与列(6)的结果可以发现,列(2)只控制出口国/地区—时间和出口国/地区—产品固定效应,而忽视了不同产品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列(3)只控制产品—时间和出口国/地区—产品固定效应,而忽视了不同国家/地区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与列(6)的结果相比,忽视了不同产品、不同国家/地区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可能导致遗漏变量问题(如产品质量、国家政策、汇率),从而无法完全解决FTA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导致估计结果的偏差,而且忽视不同产品随时间变化的异质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差更大。
第三,实证分析中对“零值贸易”问题的处理是关键,传统方法不仅无法获得一致有效估计,而且严重低估结果。比较列(4)、列(5)与列(6)的结果可以发现,常用的直接剔除“零值贸易”以及对“零值贸易”加上1进而取对数的处理方式,其估计结果均存在明显的低估,而且“零值贸易”加上1进而取对数的处理方式造成的估计偏差更大。Silva和Tenreyro(2006)指出,由于随机扰动项的异方差和“零值贸易”使得传统利用对数线性模式来估计引力模型的结果是非一致的,而PPML技术可以获得一致有效估计。Larch等(2019)指出,当样本存在大量的低贸易流量和贫穷国家时,存在更加严重的异质性,而取对数的处理方式无法克服这种异质性。此外,基于PPML估计结果得到的伪R2达到0.981,明显高于对数线性估计得到的0.779和0.838。上述对比结果表明,合理处理“零值贸易”问题对估计结果影响非常大。
第四,本文的估计结果不仅有效,而且还处于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从列(6)的结果可知,在控制出口国/地区—时间、产品—时间和出口国/地区—产品三向固定效应后,关税减让幅度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预期相符。该估计系数为6.028,即关税减让幅度引致的产品价格每下降1%,进口增加6.028%。这说明中国实施FTA战略,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显著促进了进口贸易。本文估计结果与当前大多数相关研究的结果非常接近。例如,Broda和Weinstein(2006)估计中国的进口替代弹性为6.189,Kee等(2008)估计中国简单平均进口需求弹性为7.26,陈勇兵等(2011)估计1995—2004年中国进口替代弹性中位数为3.652,Jean和Bureau(2016)估计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对农产品进口的估计系数在3.86—6.49区间。
(二)不同关税减让幅度的影响
在FTA中,企业是否利用FTA主要取决于遵守原产地规则所增加的执行成本与获得关税减让优惠的收益,因此,虽然前面的估计结果发现关税优惠对进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还没回答到底关税减让幅度达到多少才可能对贸易起到促进作用。据此,本文进一步将关税减让分为0%—5%、5%—10%、10%—15%、15%—20%和20%及以上5个等级,并将其与关税减让幅度交叉相乘,以捕捉不同关税减让幅度的影响。
同样利用高维固定效应PPML估计技术对式(2)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图1。可以发现:第一,关税减让幅度在5%以内对进口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而只有关税减让幅度大于5%才对进口有显著促进作用,估计系数在5.905—7.230区间。该结果与Jean和Bureau(2016)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同时,与前文判断一致,这样的结果说明,只有关税减让幅度达到一定程度,至少应该弥补遵守原产地规则所导致的执行成本,关税减让才可能对贸易产生作用,这也意味着其他相关研究直接利用关税来衡量FTA的贸易效应可能不够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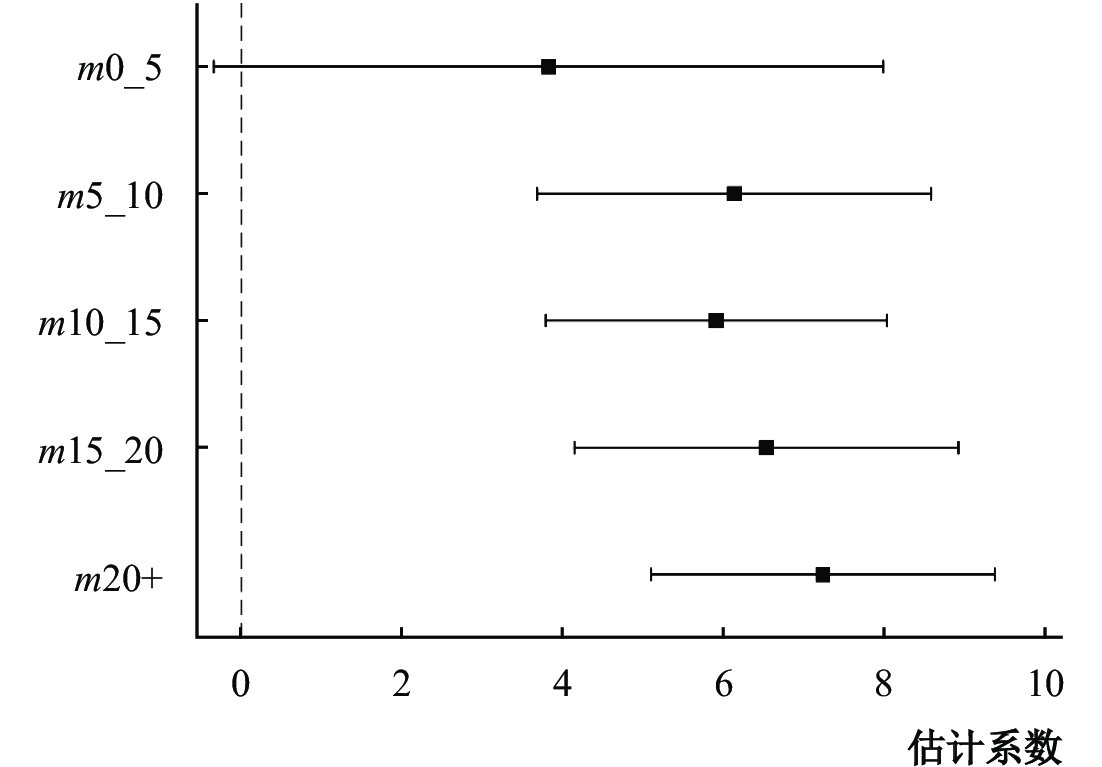
|
| 图 1 不同关税减让幅度的估计结果 注:m0_5表示关税减让幅度与关税减让0%—5%的交叉项,其他类似。 |
第二,关税减让幅度在5%—10%区间,对进口有显著促进作用,这间接说明遵守原产地规则的执行成本在5%—10%区间。这样的估计结果与部分研究结果一致。例如,吕建兴和曾寅初(2018)发现遵守农产品原产地规则的平均执行成本为7.41%,Cadot等(2006)估计NAFTA和泛欧优惠协定的执行成本分别为6.8%和8%;但韩剑等(2018)通过估计原产地规则对FTA使用率的影响,测算得到2014年中国—瑞士FTA的使用成本为2.77%。与之相比,本文的估算结果明显大于韩剑等(2018)的结果,可能原因是:①该文仅测算中国—瑞士FTA的情况,属于单样本分析,不具有总体代表性,而本文则是考虑了所有FTA。②该文仅分析中国—瑞士FTA关税立即降为0的情况,而忽视了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的情况(即忽视了关税减让表中的B、C1、C2和D减让模式)。由于具有一定过渡期的产品可能是相对敏感的产品,相应的原产地规则可能更为严格,相应的执行成本更高,因此忽略这些产品,可能导致结果低估。
第三,在5%—20%区间,随着关税减让幅度的增加,关税减让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呈现逐步增强的特征,也即关税减让幅度越大,企业利用FTA的积极性越强,其对进口的促进也越明显。这与现实相符,如前文所述,企业利用FTA要遵守原产地规则,由此要追踪和记录产品的生产、增加值等信息,而且可能要调整生产和贸易策略,为此需要支付额外的执行成本,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这样的执行成本总体呈下降趋势,因此关税减让幅度越大,企业获得的优惠将越多,从而有利于推动贸易的增长。
(三)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的影响
为了符合GATT的要求,FTA中大部分产品都会大幅度降税,但是为了给国内进口竞争型产业提供一定缓冲期,很多产品的关税减让存在一定的过渡期。Baier和Bergstrand(2007)发现,FTA生效10年后双边贸易将增加100%,这样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大量产品只有在一定过渡期后关税减让才生效。据此,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过渡期关税减让对进口的影响。
如前文一样,利用PPML估计技术对式(3)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图2。可以发现,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关税优惠对进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估计系数分别为9.531、4.071和3.946。这说明:第一,关税立即降为0时关税优惠对进口的促进作用最大,而2—5年关税减让过渡期和6年及以上过渡期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差异不大。这样的结果至少说明关税立即降为0和不同过渡期关税减让对进口的作用具有异质性,这也进一步表明区分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分析关税减让作用的合理性。Besedes等(2020)也发现FTA贸易效应主要来自关税立即降为0的产品,而不是有一定关税减让过渡期的产品。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为了符合GATT关于建立FTA的要求,大部分FTA在生效后会对大部分商品实行降税,而且优惠幅度也较大,从而对进口的促进作用较大;虽然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有过渡期,但是这些产品的数量相对较少,关税减让幅度也并没有更大,因此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可能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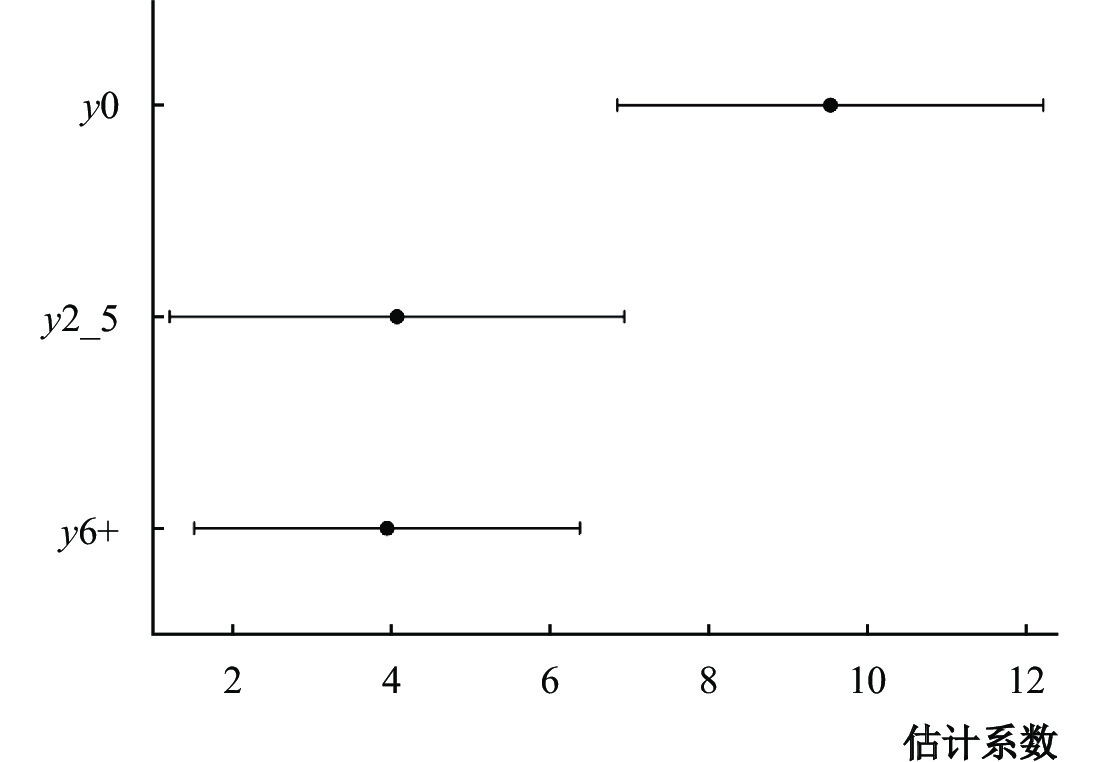
|
| 图 2 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的估计结果 注:y0表示关税立即减让,y2_5表示过渡期在2到5年,y6+表示过渡期在6年及以上。 |
第二,若将2—5年关税减让过渡期和6年及以上过渡期的估计系数简单相加,其与关税立即降为0的估计系数差异不大,这说明当过渡期到期后关税减让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可翻近一倍。可能的解释是,政府为了弱化大量进口对国内敏感产业的冲击,针对部分产品(特别是敏感产品)设定一定时期的关税减让过渡期,当这些产品开始降税,其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将增强。这样的结果与Baier和Bergstrand(2007)的发现基本一致。
(四)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不同关税减让幅度的影响
上述结果只是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的平均结果,无法刻画不同关税减让幅度的异质性。为此,本文将关税减让过渡期与关税减让幅度进行交叉相乘,以此揭示不同过渡期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对进口影响的异质性。同样利用PPML 估计技术对式(4)进行估计。图3结果表明,关税立即降为0时,10%—15%和15%—20%的关税减让幅度都对进口有显著促进作用,估计系数分别为10.241和5.183;在2—5年过渡期,10%—15%、15%—20%和20%及以上的关税减让幅度都对进口有显著促进作用,估计系数分别为3.826、3.877和6.455;在6年及以上过渡期,5%—10%、15%—20%和20%及以上的关税减让幅度都对进口有显著促进作用,估计系数分别为3.763、4.828和5.820;而其他过渡期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对进口的作用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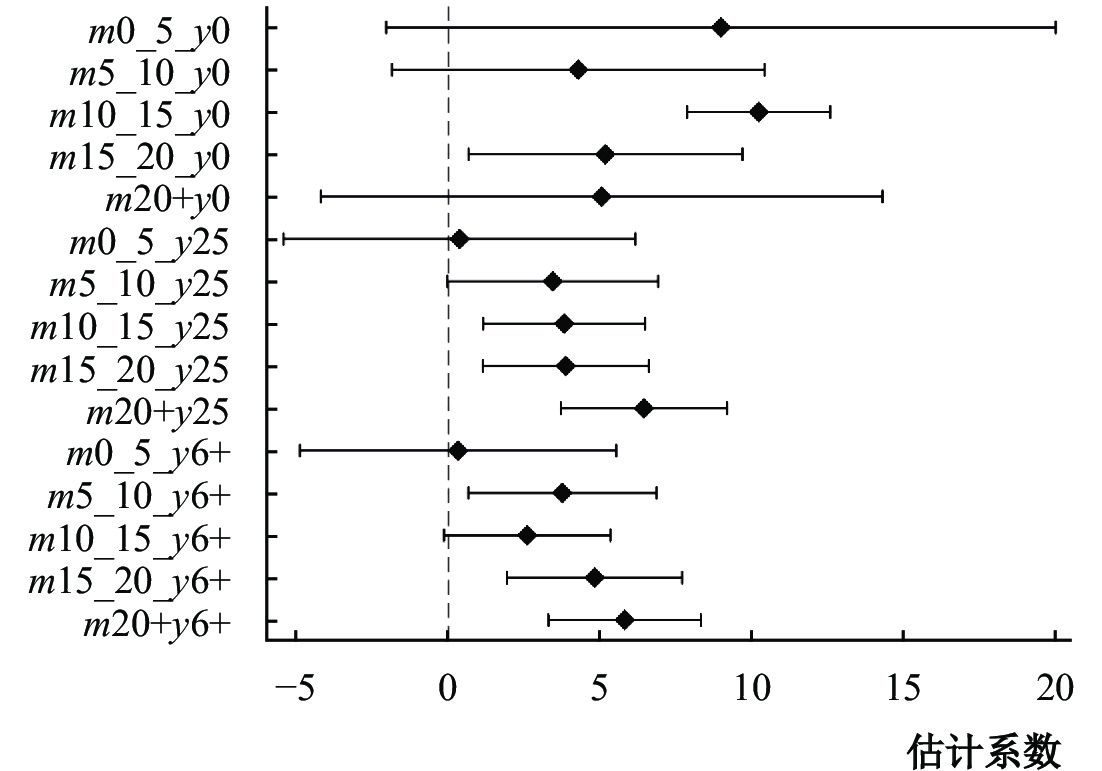
|
| 图 3 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影响的估计结果 注:m0_5_y0表示关税减让幅度在0%—5%区间与关税立即降为0的交叉项,其余类似。 |
上述结果有以下几点发现:第一,不同过渡期的关税减让幅度对进口的作用不同。在关税立即降为0和2—5年过渡期时,关税减让幅度均在10%—15%才对进口起到显著促进作用,而在6年及以上过渡期时,关税减让幅度在5%—10%时就对进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果表明,在6年及以上过渡期时,原产地规则的执行成本在5%—10%区间,而其他过渡期原产地规则的执行成本在10%—15%区间。该结果意味着不同过渡期的原产地规则执行成本是不同的。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签订FTA时就公布了相应的关税减让模式和原产地规则,虽然部分产品尚未执行降税,但是企业已经知道其原产地规则的要求,并且可以开始先追踪和记录产品的生产、成分信息,逐步调整生产和贸易策略,因此相对较长的过渡期到期后,其执行成本的门槛效应较低;反之,关税立即降为0和较短过渡期的产品,企业追踪和记录产品信息的难度较大,调整生产和贸易策略的成本较高,从而使得相应执行成本较高。
第二,不同过渡期在0%—5%区间的关税减让幅度对进口的作用均不显著。这说明关税减让幅度太小不能显著促进进口。可能的解释是,关税减让幅度在0%—5%区间,遵守原产地规则导致增加的执行成本高于所获得的优惠,因此企业不会选择利用FTA。同时,关税立即降为0且关税减让幅度达20%及以上的进口促进作用也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正如Jean和Bureau(2016)所指出的,虽然关税立即降为0导致关税减让幅度大幅增加,但受限于企业供给能力和生产与贸易策略的调整成本,无法同比例增加供应。Manchin和Pelkmans-Balaoing(2008)也发现,当东盟FTA关税减让幅度达到较高幅度时,关税减让对贸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五)产品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属性产品的竞争优势、在国民产业中的地位以及贸易策略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为保障国内的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可能对部分战略性产品设置较低的关税减让幅度和较长的过渡期。据此,本文根据产品属性将产品分为农产品和工业品,根据产业上下游关系将产品分为中间品与非中间品,根据战略属性将产品分为战略品和非战略品,⑨以考察不同产品关税减让的进口效应。
由图4可以发现,关税减让对农产品的进口影响不显著,对工业品、中间品、非中间品、战略品以及非战略品均具有显著的进口促进效应。可能的解释是,受制于FTA大范围产品大幅度降税的要求,这类产品(特别是部分敏感产品)无法继续利用关税进行保护,反而采取更强和更为隐蔽的非关税壁垒加以保护,因此关税优惠的作用被抵消。Garred(2018)发现,进口关税的大幅下降会导致贸易限制的增加,以维持之前的贸易政策;Bown和Tovar(2011)、Limão和Tovar(2011)也发现非关税壁垒是关税的主要替代措施。关税减让对中间品的进口促进作用小于其对非中间品的促进作用。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积极主动进口诸如消费品、资本品等非中间产品以满足国内多样化、高质量的需求。有意思的是,关税减让对战略品与非战略品的进口促进作用基本相当。本质上,以保护国内敏感产业为目的而设置的战略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会受到额外的保护,或者说关税减让的幅度会较小、过渡期会相对较长。这样的结果意味着,如果没有对战略品进行额外的保护,那么其面临的进口冲击与非战略品是一样的。

|
| 图 4 不同产品关税减让幅度的估计结果 |
从表2列(1)与列(2)的估计结果来看,关税减让对农产品进口有显著促进作用的门槛为15%以上的关税减让幅度,而对工业品进口促进作用的门槛为5%。可能的解释是,在中国FTA中,农产品的原产地规则大多以境内原产和“章”的变化(HS2位码的变化)为主,这些原产地规则限制程度较高,当关税减让幅度较低时无法弥补其遵守原产地规则所付出的执行成本。这样的结果也意味着,从进口保护策略上对部分敏感农产品设置中低幅度的关税减让,并不会对国内相应产业产生较大冲击。反之,关税减让对工业品进口的门槛较低,这与中国整体加工贸易的贸易模式相关,为此在FTA中主要设置“目”的变化且区域价值成分大于45%、“章”的变化且排除部分产品等限制指数相对较低的原产地规则。从估计系数上看,15%—20%和20%及以上的关税减让幅度对农产品进口的作用基本相当,但对于工业品而言,表现出关税减让幅度越大则进口替代弹性越大的特征。
| (1) | (2) | (3) | (4) | (5) | (6) | |
| 农产品 | 工业品 | 中间品 | 非中间品 | 战略品 | 非战略品 | |
| m0_5 | −4.713(4.241) | 4.157(2.617) | 8.730**(3.403) | 3.016(3.096) | −2.907(5.904) | 4.569*(2.655) |
| m5_10 | −0.456(2.644) | 6.127***(1.549) | 9.937***(2.230) | 5.851***(1.862) | 0.733(3.266) | 6.379***(1.621) |
| m10_15 | 1.452(2.021) | 5.951***(1.347) | 2.422(2.250) | 5.901***(1.452) | 5.132**(2.499) | 5.624***(1.470) |
| m15_20 | 3.257*(1.794) | 6.462***(1.807) | 0.744(2.574) | 6.568***(1.859) | 2.702(2.494) | 6.313***(2.233) |
| m20m | 3.086**(1.476) | 7.956***(1.518) | 4.166*(2.395) | 7.425***(1.474) | 5.060**(2.063) | 1.804(2.148) |
| cons | 13.402***(0.045) | 13.467***(0.009) | 12.131***(0.020) | 13.794***(0.012) | 12.343***(0.047) | 13.535***(0.010) |
| N | 290 295 | 2 816 733 | 908 540 | 2 133 943 | 7 812 16 | 2 261 227 |
| pseudo R2 | 0.994 | 0.987 | 0.981 | 0.990 | 0.987 | 0.987 |
| 注:m0_5表示关税减让幅度在0%—5%之间,其余类似。 | ||||||
从列(3)与列(4)的估计结果来看,0%—5%、5%—10%和20%及以上的关税减让幅度显著促进了中间品的进口。这样的结果与当前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2/3以及中国以进口加工再出口的贸易模式相符,这也体现了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中间品的积极开放态度。而关税减让对非中间品的进口促进效应门槛为5%的关税减让幅度,这说明非中间品的原产地规则执行门槛在5%及以上。此外,从估计系数来看,5%以内和5%—10%的关税减让幅度对中间品进口的促进作用在增大,但当关税减让幅度达到20%及以上时,关税减让的促进作用反而减少。而对于非中间品而言,表现出关税减让幅度越大则进口促进作用越明显的特征。
从列(5)与列(6)的估计结果来看,只有达到10%—15%的关税减让幅度才能对战略品进口有促进作用,这表明较低的关税减让幅度对战略品进口的作用不明显,这也意味着中国利用关税幅度来保护战略品免受进口冲击是有效的。而对于非战略品而言,关税减让引致的进口门槛很低,只要有一定幅度的关税减让,就能显著促进进口,这与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和满足国内多样化需求的战略相关。
表3进一步考察了不同过渡期对不同产品进口的影响。列(1)与列(2)的结果表明,2—5年的关税减让过渡期对农产品进口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关税立即降为0和6年及以上的关税减让过渡期对农产品进口的作用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关税立即减让可能受限于原产地规则的执行成本,导致关税立即降为0的进口效应不明显,而过渡期6年及以上的进口作用不明显可能是由于较长的过渡期使得国内农业生产能较好地应对冲击,从而使得进口产品的优势不大。这意味着在进口保护策略上,对农产品可采用关税立即减让和过渡期6年及以上的保护措施。
| (1) | (2) | (3) | (4) | (5) | (6) | |
| 农产品 | 工业品 | 中间品 | 非中间品 | 战略品 | 非战略品 | |
| y0 | 5.491(4.073) | 9.555***(1.640) | 5.849*(3.113) | 9.523***(1.696) | 10.694***(2.715) | 9.064***(1.637) |
| y2_5 | 6.873***(2.378) | 3.786*(1.993) | 5.208**(2.229) | 4.540**(2.208) | 6.142***(2.251) | 2.443(1.760) |
| y6m | 2.337(1.565) | 3.816**(1.571) | 9.090***(2.606) | 3.190*(1.810) | 4.284*(2.383) | 2.488(1.776) |
| cons | 13.3678***(0.037) | 13.471***(0.009) | 12.129***(0.019) | 13.802***(0.012) | 12.337***(0.045) | 13.544***(0.010) |
| N | 290 295 | 2 816 733 | 908 540 | 2 133 943 | 781 216 | 2 261 227 |
| pseudo R2 | 0.994 | 0.987 | 0.981 | 0.990 | 0.987 | 0.987 |
| 注:y0表示关税减让立即降为0,其余类似。 | ||||||
列(3)与列(4)的结果表明,过渡期越长,关税减让对中间品的进口促进作用则逐渐增大,而对非中间品的促进作用则逐渐减小。可能的解释是,中国虽然以进口加工再出口的模式参与全球贸易从而扩大中间品的进口,但是可能对部分涉及中国未来竞争力的产品设置较长的过渡期,当这些产品的过渡期到期后,可能会释放进口促进效应。而对于非中间品而言,随着关税减让的红利逐渐消失,相应的进口效应也逐渐减弱。
列(5)与列(6)的结果表明,过渡期越长,关税减让对战略品的进口促进作用在逐渐变小,而对非战略性产品的进口促进作用仅限于关税立即降为0。可能的解释是,为了保护涉及国内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的战略性产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会设置一定时期的过渡期,而这些战略性产品往往不具有比较优势,为此当这些产品的过渡期到期后,可能会产生进口促进效应,但是其估计系数逐渐变小也意味着不同过渡期的保护是有效果的。而对于非战略品而言,并不会设置大量的关税减让过渡期进行保护,为此在关税立即降为0时贸易效应就开始显现。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中国大举推进FTA建设、构筑新型开放格局的背景下,科学评估FTA贸易效应是一项非常紧迫的工作。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国家/地区—产品—时间”层面的大样本数据来评估中国FTA的进口效应,在解决FTA贸易效应测度中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的基础上,利用DID、DDD和高维固定效应PPML技术估计了中国FTA关税减让对进口的影响。研究发现:(1)FTA关税减让显著促进了进口,关税减让引致产品价格下降了1%,进口增加了6.03%,这说明关税引致的进口替代弹性为6.03。而且5%—10%的关税减让幅度对进口有显著促进作用,这间接表明了FTA原产地规则所具有的执行成本。(2)不同关税减让幅度和不同过渡期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随着关税减让幅度的增加,进口促进作用呈逐步增强的特征,以及随着关税减让过渡期的延长,进口促进作用总体呈下降趋势,但过渡期结束后累计关税减让对进口的促进作用增加1倍。(3)不同属性产品对FTA关税减让幅度和过渡期的进口反应呈现不同的特征,而且农产品与其他产品的差异很大。
上述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含义:(1)中国实施的FTA战略,降低了关税壁垒,促进了进口贸易,满足了国内对高质量产品和多样化产品的需求,但同时进口边境壁垒的下降所引致的进口竞争可能冲击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从而导致部分企业退出市场、成本加成降低,因此FTA引致的进口贸易自由化对国内福利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2)出口企业要享受FTA的关税优惠,需要遵守原产地规则,而遵守原产地规则需要额外支付一定的成本。本文的经验研究表明,低于5%的关税减让幅度对进口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从扩大开放的角度出发,对这类产品可适当放开保护,从而为推进WTO的多边贸易谈判做出表率。(3)随着过渡期的延长,关税减让对进口的作用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在FTA中设置关税减让过渡期对国内进口竞争型产业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因此在未来FTA谈判和贸易政策制定中可策略性地强化使用过渡期这个条款。(4)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和关税减让幅度的搭配组合对进口的影响呈现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在未来FTA谈判和贸易政策制定中,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数量和时期的多种搭配组合,从而科学设置敏感产业的保护措施,放开没有必要保护的且能够满足国内需求的产业,进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① 根据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从当前已生效FTA的进口6589.79亿美元,占中国总进口的31.85%;出口5720.31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的22.89%。
②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MFN关税和FTA优惠关税的变化趋势,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不同产品和不同关税减让过渡期的关税减让幅度的具体情况;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④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不同FTA不同过渡期、不同减让幅度以及税目占比情况;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⑤ 为简化表达,关税减让幅度已是关税减让与否(treated)和关税减让生效先后(post)的交乘,下同。
⑥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详细的原产地规则限制指数,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⑦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⑧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出DID有效性和动态性检验、PSM以及核心解释变量滞后1期的估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⑨ 战略品的数据来自吕建兴等(2021)。
| [1] | 陈勇兵, 李伟, 钱学锋. 中国进口种类增长的福利效应估算[J]. 世界经济, 2011(12): 76–95. |
| [2] | 韩剑, 王灿. 自由贸易协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对FTA深度作用的考察[J]. 国际贸易问题, 2019(2): 54–67. |
| [3] | 韩剑, 岳文, 刘硕. 异质性企业、使用成本与自贸协定利用率[J]. 经济研究, 2018(11): 165–181. |
| [4] | 吕建兴, 王艺, 张少华. FTA能缓解成员国对华贸易摩擦吗? ——基于GTA国家—产品层面的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a(5): 114–134. |
| [5] | 吕建兴, 曾寅初. 中国FTA中原产地规则例外安排对农产品进口的影响[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11): 132–144. |
| [6] | 吕建兴, 曾寅初, 张少华. 中国自由贸易协定中市场准入例外安排的基本特征、贸易策略与决定因素——基于产品层面的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21b(6): 80–98. DOI:10.3969/j.issn.1006-480X.2021.06.005 |
| [7] | Anderson J E, Van Wincoop E.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1): 170–192. DOI:10.1257/000282803321455214 |
| [8] |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Clance M W.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s[J]. Journal of Develop- ment Economics, 2018, 135: 587–608. DOI:10.1016/j.jdeveco.2018.08.014 |
| [9] |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Do free trade agreements actually increase members’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1(1): 72–95. DOI:10.1016/j.jinteco.2006.02.005 |
| [10] |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Feng M. 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s and th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93(2): 339–350. DOI:10.1016/j.jinteco.2014.03.005 |
| [11] | Besedes T, Kohl T, Lake J. Phase out tariffs, phase in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0, 127: 103385. DOI:10.1016/j.jinteco.2020.103385 |
| [12] | Bown C P, Tovar P. Trade liberalization, antidumping, and safeguards: Evidence from India's tariff reform[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6(1): 115–125. DOI:10.1016/j.jdeveco.2010.06.001 |
| [13] | Broda C, Weinstein D E. Glob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varie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6, 121(2): 541–585. DOI:10.1162/qjec.2006.121.2.541 |
| [14] | Cadot O, Carrère C, De Melo J, et al. Product-specific rules of origin in EU and US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An assessment[J]. World Trade Review, 2006, 5(2): 199–224. DOI:10.1017/S1474745606002758 |
| [15] | Garred J. The persistence of trade policy in China after WTO access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4: 130–142. DOI:10.1016/j.jinteco.2018.06.001 |
| [16] | Head K, Mayer T. Gravity equations: Workhorse, toolkit, and cookbook[J].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4: 131–195. |
| [17] | Jean S, Bureau J C. Do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eally boost trade? Evidenc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s[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6, 152(3): 477–499. DOI:10.1007/s10290-016-0253-1 |
| [18] | Kee H L, Nicita A, Olarreaga M. Import demand elasticities and trade distortion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8, 90(4): 666–682. DOI:10.1162/rest.90.4.666 |
| [19] | Larch M, Wanner J, Yotov Y V, et al. Currency unions and trade: A PPML re-assessment with high-dimensional fixed effects[J].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9, 81(3): 487–510. DOI:10.1111/obes.12283 |
| [20] | Limão N, Tovar P. Policy choic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ommitment via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5(2): 186–205. DOI:10.1016/j.jinteco.2011.06.002 |
| [21] | Manchin M, Pelkmans-Balaoing A O. Clothes without an emperor: Analysis of the preferential tariffs in ASEAN[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8, 19(3): 213–223. DOI:10.1016/j.asieco.2008.03.001 |
| [22] | Roh J, Park J H.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rules of origin requirements of KOREA-US FTA with a new measure of the requirements[J]. The Korean Economic Review, 2014, 30(1): 163–190. |
| [23] | Silva J M C S, Tenreyro S. The log of gra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6, 88(4): 641–658. DOI:10.1162/rest.88.4.641 |
| [24] | Urata S, Okabe M. Trade creation and diversion effect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 product-level analysis[J]. The World Economy, 2014, 37(2): 267–289. DOI:10.1111/twec.12099 |
| [25] | Yotov Y V, Piermartini R, Monteiro J A, et al. An advanced guide to trade policy analysis: The structural gravity model[M]. Geneva: WTO, 2016. |

